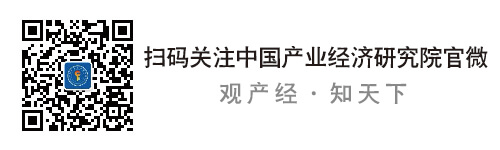休谟
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
"理性是且应当只是激情的奴隶。"
论灵魂的非物质性
人性论·节选
译者:王绚祯
我们已经发现,在任何一个有关外部对象的系统,以及在我们想象中清晰明确的物质观念里,都有这样的矛盾和困难,那么在有关内心知觉的假设中,我们自然而然会预想遇到更大的困难和矛盾,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后者更加模糊不定。但是,这种预想是错的。理智世界虽然十分晦涩难懂,但并没有那些我们在自然世界中所发现的那般矛盾。我们对于理智世界的感知都自相符合;而对于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我们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的确,如果我们倾听某些哲学家的言论,会听到他们想要减少无知的誓言;不过我害怕,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就有可能会陷入这个题目本并不具有的矛盾中。这些哲学家善于推理,他们提出疑问:我们的知觉到底是物质实体所"固有"的还是精神实体所"固有"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所知的最佳方法就是给这些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你觉得'实体'和'固有'分别指的是什么?"在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合理地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发现,涉及物质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涉及精神,这个问题不仅同样难以回答,还增加了一些特殊的困难。任何观点都来自先前的印象,倘若我们对精神实体有任何想法,我们一定先对其有一个印象;如果无法想出之前的印象,那么我们便难以形成观点。因为,一个印象若非与这个实体类似,怎么可以代表这个实体呢?而按照目前讨论中的哲学理论,倘若先前的印象不具有任何这一实体的特殊属性,怎么可能与这一实体相似呢?
但是,如果抛开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的问题不谈,转而思考现实是什么,那么我希望,那些认为我们已经形成了关于精神实体观念的哲学家,可以指出这一观念来源的印象,并且清楚地说出这一印象是如何运作的,是由哪个对象得来的。它是感觉的印象,还是想法的印象?是愉悦的印象、痛苦的印象,抑或是漠然的印象呢?我们是时刻拥有这个印象,还是只是偶尔想起呢?倘若只是偶尔想起,那么我们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想起,为什么会想起?
倘若有人逃避回答这些难题,转而声称"一个实体"的定义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在的东西,并且声称这种定义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我会回答,这个定义可以用于任何可能想象出的事物,但它无法用来区分实体和偶然,也无法区分灵魂和感知。原因如下。首先是这样一条原则:
任何事物都可以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凡是可以区分的事物都可以在想象中彼此分离--可以单独想出来。
我们已知的另一条原则是:
凡是可以明确设想出来的事物都是存在的,并且物体是以何种方式被明确设想出来的,就以何种方式存在。譬如,物体在想象中是彼此分离的,那么它们在现实中就确实是彼此分离存在的。
我从这两条原则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既然我们所有的感知都有所不同,与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也都有所不同,加之我们的感知是独特且可以彼此分离的,也可以考虑或构想为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我们的感知就是可以独立存在并且不必相互依靠的。因此,照上述的定义,我们的感知都是实体。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最初的印象入手,还是从定义入手,我们都无法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实体概念;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个充分的理由,让我彻底不再去思辨灵魂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也让我十分反感这一问题。除了自己的知觉,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实体和知觉截然不同,因此我们不知道实体是什么。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只有依靠某种"固有"知觉的事物,知觉才可以存在;但是知觉似乎不需要依靠别的东西就可以存在。因此我们不清楚"固有"指什么。如果情况如此,我们如何去回答"我们的知觉到底是物质实体所'固有'的还是精神实体所'固有'的"这个我们都不了解其含义的问题?
知觉的空间位置
有一个观点,人们通常用它来说明灵魂的非物质性,在我看来是值得注意的。这个观点是:
凡是占有空间的事物,都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凡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就可以在现实或在想象中被分离。但凡是可分的事物,都不可能与完全不可分割的思想或感知联系在一起。如果真的有这种联系,那么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位于这占有空间、可分离的物体的左边,还是位于其右边?位于它的前面还是后面?抑或位于它的表面还是中间?如果你无法确定这些疑问的答案,那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倘若思想或感知与某件占有空间的事物相联结,那么一定存在于这件事物界线内的某个位置--不是在其某一个部分,就是在其每一个部分。若在其某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不可分的,而感知仅仅与这一部分联结而非与这整件事物联结;若在其每一部分,思想应该占有一定空间,既可分又不可分,就像物体一样,这是十分荒唐而自相矛盾的。有人能想象出一种一码长、一英尺宽、一英寸厚的情感吗?因此,思想和空间是完全互斥的两种性质,永远无法一并而谈。
这一论证并不影响关于灵魂实体的问题,而只影响其与空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大体上考虑哪些物体可以占有空间,哪些物体不能占有空间。这是个有趣的难题,可能引领我们得出至关重要的结论。
我们关于空间和广延的第一个概念完全来自视觉和触觉;只有有颜色和有形状的物体可分为若干部分,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传达了空间观念。你可能会说,味道也有若干部分,因为味道可以减弱或加强;但味道的减弱和加强与一个可见物体的减小和增大有所不同。你可能还会说,我们通过听觉感受到距离--也就是广延;但我们同时听到好几个声音时,我们只能通过习惯和思考,对发出声音的不同物体间的空间关系形成一个观念。任何事物,只要存在于某个地方,就一定占有空间,否则就是没有结构和内部复杂性的数学点。占有空间的事物必然有一定的形状--正方形、圆形、三角形,但没有任何形状是属于欲望、属于印象或观念的,除了与视觉或触觉相关的印象或观念。尽管一个欲望并不可分,但我们不应将其看作为一个数学点。否则,一个欲望就可以和其他三个或四个欲望一起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有一定长度、宽度和厚度的复杂体;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鉴于这些论证,如果我提出什么观点,为形而上学家所谴责,为他人视作与最确定的人类原理相矛盾,你应该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想提出的观点就是:一个对象可以存在,但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大多数存在的事物,都确实并且必然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一个物体的成分无法组合形成形状或大小,其整体与其他物体的关系也不符合我们的远近距离观念,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对象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显而易见,除了视觉和触觉的感知和对象之外,我们所有的感知和对象都符合这种情形。味道或声音不可能呈现圆形或方形;道德反思也不可能位于一种情感的左边或者右边。这些对象和感知非但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场所,而且是绝对与其不容的;我们甚至想象不出它们存在于任何空间位置。
感知并非由若干部分组成,也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不可能与物质或物体--占有空间且可分离的东西--在空间上有任何联系,因为联系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特质之上。但我现在没有必要说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对象空间位置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形而上学关于灵魂本质的争论中,而且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设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无花果,另一头有一颗橄榄:当我们对这两个实体形成复杂的观念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们具有不同的味道,很明显我们是把这些特质与有颜色且可触摸的性质合并、结合了起来。我们认为,无花果的苦味和橄榄的甜味存在于可见的物体之中,因此长桌可以将它们分开。这一假设不同寻常,但也十分自然,因此我们应该去思考它产生的原理。
虽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东西无法与占据空间的东西在空间中结合,但它们之间可以建立许多其他的关联。因此,一个水果的味道和气味与颜色和可触性不可分割;无论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这些性质必然同时存在。这些性质不仅仅以一般的形式同时存在,而且还在我们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味道和气味同时出现在我们心里;只有当我们靠近了占有空间的物体时,我们才能闻到气味,尝到味道。因此,我们自然推测出,物体是我们闻到气味和尝到味道的原因,得出了占有空间的对象和不在任何特殊场存在的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它们出现时间所具有的连续性;这在我们的心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想到一个相关性质时,会立刻联想到另一个性质。这还不是全部,我们不仅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性质联想到另一个性质,我们还试图给它们建立进一步的联系,即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场所,这让我们的联想发生得更加容易、自然。这是出于人性的一种特质(下文会谈论,在恰当的地方我将详细说明),当我们用某种联系将对象结合起来时,我们会强烈渴望找到更多的联系,让其结合更加完整。
但是无论我们对于将一个物体(例如无花果)和它的味道在空间上进行结合的问题持有怎样混淆的观点,当我们考虑起这种结合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结合不仅莫名其妙而且自相矛盾。让我们问自己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我们想象里包含于无花果中的味道,是存在于无花果的每一部分,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某一部分中呢?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会不知所措,然后发现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不能回答味道只在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经验让我们相信,每一部分的味道都一样。我们回答味道在无花果的每一部分也不好,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假设味道是有形状和大小的,这很荒谬且难以理解。因此在这里,我们被两条原则拉向相反的方向--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将味道与无花果结合在一起,而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这两条原则将我们左右拉扯,我们没有否认任何一条,我们陷于这个问题的迷惑与晦涩之中,以至于渐渐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无花果的味道存在于其界限内,充满整个无花果而不占据任何空间,完全存在于每一个部分之内而无须分离。简而言之,在我们日常最普通的思考中,我们应用了经院哲学派的原则--totumintoto,ettotuminquailibet(拉丁文,意为"全体既存于全体,又存在于各部")。大意是说,一个事物存在于某个地方,却也不在那个地方,这听起来似乎骇人听闻。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些荒谬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试图赋予场所一样完全不适合它的东西;而我们之所以要试图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想要在因果关系和时间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将对象归于同一个空间之内,使其结合更加完整。但是如果理性强大得足够克服偏见,那么它在此必然也能取得胜利。因为对于像感情、味道和气味这样事物而言,以下是仅有的几种可能性:
●它们不需要任何场所就可以存在。
●它们有形状和大小。
●它们与占有空间的对象结合,然后整体存在于整体之中,而整体也存在于每一部分。
第二种和第三种假设的荒谬充分反证了第一种假设的正确性,并且我们想不到第四种假设了。那么假设这些东西都是以数学点的方式存在又会如何呢?其实这并不算是第四种假设,因为它可以归类到第二种假设当中:它假设不同的感情可以放进一个圆圈内,若干种味道可以与若干声音结合,形成一个十二立方英寸的物体;这实在荒谬可笑。
然而,虽然站在这一角度,我们不得不去批判唯物主义者,他们将一切思想都与占有空间的物体结合起来,但是稍加反省,我们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去批判他们的反对者,他们将所有的思想都与一个简单而不可分的实体结合起来。最通俗易懂的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外部的对象无法直接被大脑感知;这个感知过程必须通过印象或感知的介入才能完成。此时呈现在我面前的桌子只是我的感知,其所有的属性都是感知的属性。现在,所有属性中最明显的一个属性就是它占有空间。感知由若干部分构成,这些部分以一定的方式排序,给予我们距离、长度和宽度的概念。这三个维度的界限建构了我们所谓的形状。这种形状是可移动、可分离且可分割的。移动性和可分性是占有空间的物体的所独有的性质。为了终止所有的争论,广延这一观念仅仅是由一个与其完全符合的印象得来的。我们说广延性这一观念与某物"符合",其实是说这一观念是占有空间的。
现在轮到唯物主义的自由思想者自鸣得意了。他们发现一些印象和观念真的占有空间后,就可以质问他们的反对者:"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简单不可分的主体与一种占有空间的知觉聚合在一起?"神学家的全部论证都在此转向他们自己。唯物主义者们早就向他们提出:"不可分的知觉是在占有空间的物体的左边还是右边?",而现在,唯物主义者可以提出:"不占有空间的主体(或者你也可以说非物质的实体)是在占有空间的知觉的左边还是右边?是在这个特定的部分呢,还是在那个特定的部分?是在每一部分呢,还是只在某一个部分,但又没有抛弃其他部分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不是荒唐至极,就是为唯物主义者所用,以说明不可分的知觉与占有空间的实体是如何结合的。
知觉的实质性基础(斯宾诺莎)
借此机会,我再次提出灵魂的实体问题。我虽然认为这一问题完全无法理解,但还是不禁要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因此我提出:
认为实体是非物质、简单而不可分的,这是真正无神论的信条,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所有让斯宾诺莎臭名昭著的无神论观点。
通过这一观点,我希望至少能够获得一个优势,那就是让我的反对者发现,他们的指责可以轻易反过来针对他们自己时,他们便没有任何借口认为我的观点是错的。
斯宾诺莎无神论的基本原则就是宇宙的单纯性--宇宙没有部分,以及其统一性--思想和物质都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所固有。斯宾诺莎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实体,实体是单纯不可分的,也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位置,因为它存在于每一处。无论我们通过感官在外部世界发现了什么,还是通过反思在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什么--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必然存在的实体的属性,没有任何分离或特殊的存在。这张桌子和那把椅子不是两件独立的东西,它们只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东西--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罢了。灵魂的每一种情感,物质的每一种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为同一个实体所固有;它们保持着各自独特的属性,但并不会导致他们为不同的实体所固有。同一个基体(substratum)(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属性,可以改变内在的属性但不改变其自身。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一切自然的差异,都不能让这个完美、单纯、统一的实体产生一丝变化。
我相信,对于这著名的无神论所作出的以上简述,足以说明我现在的目的。无须继续深入到晦涩难懂的部分,我就可以证明,斯宾诺莎可怕的假设与深入人心的灵魂的非物质性的观点相差无几。为了阐明这点,让我们回忆一下前面(第二章第六节)所提到的,每一个观念都是来自先前的知觉,我们不可能产生一个与知觉种类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存在的事物的观念,也不可能与知觉完全不同种类。无论我们假设知觉与外界事物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仍然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要么认为外界对象就是一种知觉,要么认为外界的对象仅仅是没有相关项的一种关系,即认为它仅仅是与知觉有关的什么东西。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初看可能是一种诡辩,但如果你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个结论可靠且令人满意。我从以下这点说起: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对象和印象在种类上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我们无法想出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得出任何有关印象相互联系或者自相矛盾的结论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对象;但是,我们得出的有关对象的结论,一定能应用于印象。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对象理应与其印象不同;因此,倘若我们从印象开始推断,我们不能确定推断所依据的细节是印象与对象共有的;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对象仍有可能与印象有所差别。但反过来就不同了:倘若我们从对象开始推断,我们得出的结论一定能应用于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对象的属性是推测的基础,而这属性至少是能够被大脑想象出来的(否则推测便无从开始),又由于所有的观念都来源于印象,因此除非这种属性是印象与对象所共有的,否则我们的大脑就无法想象出它来。综上,我们可以建立一条确定的原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对象间发现印象所不具有的相关性或不相容性--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印象间发现对象所具有的关系,就说不准了。
我们把这一结论运用到目前的问题中。我的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存在事物系统--为了便于讨论,我不得不赋予这两个系统某种实体或寓存的基础。我首先观察的是无数事物所组成的宇宙--有太阳、月亮、大地,有大海、植被、动物,还有人类、轮船、房屋和其他自然或人工的产物。斯宾诺莎在这里出场,然后告诉我们:
这些仅仅是属性,而寓存这些属性的主体--具有这些属性的实体--是单纯、非复合且不可分的。
然后我开始考虑另一个系统,也就是思想的宇宙,或者说我的灵魂与观念的宇宙。在这个系统里,存在着另一套太阳、月亮和星辰,植被覆盖、动物居住的大地和海洋,城镇、房屋以及山川河流--简单来说,就是我在第一个系统里发现和构想出的所有事物。我对此感到疑惑,这时神学家们出场了,他们告诉我说:
这些都是属性,这些的确是一个单纯、非复合且不可分的实体所具有的属性。
紧接着,我听到无数震耳欲聋的声音,有对斯宾诺莎假设的批判声和骂声,也有对神学家观点的掌声和赞美声!我分析这些假设,思考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一边,于是我发现这两个假设都同样的晦涩难懂,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而言,这两个假设非常相像,我们找不到哪个荒谬的地方不是二者所共有的。由于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来自印象,因此我们每一个关于对象属性的观念可以代表一个印象的属性并与其相配。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反驳斯宾诺莎的观点,发现"一个占有空间的对象是一种属性"与"寓存于实体内的是简单而非复合的东西"相矛盾,那么我们必然也同样可以在一个"对于占有空间的对象所产生的知觉或印象"与"寓存简单而非复合东西的实体"间发现矛盾。一个对象的属性,对其的每一个观念都来自一个印象,因此任何可知觉的关系,不论是关联性还是不相容性,必然是为对象与印象所共有的。
大体上看,这一论证似乎明显不存在任何疑问和矛盾。但为了将它说得更加清楚明白,让我们再详细地梳理一遍,看看我们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体系中发现的荒谬之处,是否也可以在神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发现。
首先,对于斯宾诺莎有这样的反驳:
由于根据斯宾诺莎的理论,属性并不是一个特别或独立的存在--某种存在于实体之外的东西,那么它一定和实体是一体的。因此我们认为,具有广延性的宇宙作为一种属性,寓存于一个简单、非复合的实体中,那么这个宇宙一定以某种方式与这个实体是一致的。但这又完全不可能且不可理解,除非不可分的实体为了符合广延的世界而扩散,或者广延的世界为了与不可分的实体相配而紧缩。
这番论证(与斯宾诺莎的理论相悖)在我们听起来似乎是合理的;显而易见,只要换几个名称,这番论证也同样适用于(与神学家的理论相悖)我们具有广延性的知觉和简单的灵魂实体。除了那些未知、难懂的差异,对象与知觉的观念在每个方面都一样。
对于斯宾诺莎的第二条反驳是:
我们所有对于实体的观念都适用于物质,所有对于特殊实体观念都适用于每一特殊部分的物质。因此物质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种实体,而每一部分的物质并不是特殊的属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实体。
我已经证明,我们没有完美的实体观念,而只是把"实体"当作"某样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据此,显而易见,任何知觉都是一种实体,知觉的任何特殊部分都是实体的特殊部分。因此,从这方面看,这两种假设都面临同样的困难。
第三,对于宇宙之内只存在一个单纯的实体体系这一观点,人们反驳说:
宇宙作为世间万物的支撑或者说基体,必然可以在同一时刻化为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形式。在同一时刻,圆形和方形在同一个实体内互不相容。那么,同一个实体如何能在同一时刻既变成方桌又变成圆桌呢?
我针对这些桌子的印象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然后发现其答案并没有比前者的答案更加令人满意。因此,斯宾诺莎在这方面所遭遇的尴尬境遇其实与神学家们所遭遇的境遇同样。
由此可见,我们不论采用哪一种假设,都会遭遇同样的困难。要更进一步地建立灵魂的单纯性和非物质性,就难免为危险而无法矫正的无神论铺路。不称思想为灵魂的变形或属性,而是换一个更加古老而又更加新潮的词"活动",情形也不会改变。通过活动这个词,我们表达了和所谓"抽象的属性"差不多的意思--严格来说,即与其实体相差无几且不能分离的东西,并且人们只能通过理性的区分,也就是用抽象的思维,来理解它。譬如,跳舞与舞者相差无几且密不可分,但是总体上看,我们说她在跳舞,是用抽象的思维从一个方面理解舞者。但是,通过这种从"变形"到"活动"的转变,我们面临的困难一点也没有减少。
知觉产生的原因
通过这些关于知觉的空间关系及实体的假设,让我们转向另一个比前者更容易理解、比后者更加重要的一个假设,即关于知觉产生的原因的假设。经院学派认为:
物质和运动不论如何变化,仍然是物质和运动,只是物体的位置与方向不同罢了。不论你如何频繁地分割一个物体,不论分割成什么形状,除了它的形状(也就是各部分的关系),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论你以何种方式移动一个物体,你仍然只能发现运动(也就是它与其他物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能去想象,一种圆形运动仅仅是圆形运动,而椭圆形运动则是一种情感或道德反思;或者去想象,两种球形分子撞击后会产生一种疼痛的感觉,而两种三角形分子撞击后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这太荒谬了。现在,这些不同的撞击、变化和混合是物质仅有的可以发生的改变,由于这些改变无法给我们任何思想或知觉观念,因此,我们认为知觉绝不是由物质引起的。
很少有人能够抵挡这一论证所具有的表面说服力,但驳斥它,其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我在前面大体上已经证明,我们从来感受不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任何联系,只有通过我们对于因和果永恒结合的体验,我们才能推出因果关系。现在,我们只要回顾一下:
●?两个真实的对象互不矛盾。
●?互不矛盾的对象可以永久结合。
通过这两个原则,我在第三章第15节已经指出:
如果由因及果地看待物质,任何事物可以引发任何事物,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任何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论两个对象有多类似或不似彼此,其中一个对象都有可能是或不是另一个对象产生的原因。
这显然打破了前面关于思想或知觉的起因的理论。因为,虽然在我们看来,思想和运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因果之间也没有显现出任何联系。如果在天平的一端放一个一磅重的物体,另一端放一个同样重量的物体,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发现任何建立在物体距中心距离上的运动法则,也不会发现任何思想与认知的原则。因此,倘若你声称要证明一个由因及果的假设--物体的位置永远不能引发思想,因为不论以何种方式改变物体的位置,它都只是物体的位置;那么,你一定可以通过同样的推理,得出物体的位置永远不能引发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并没有出现比前一种情形中更明显的联系。但是后面这个推论明显有违我们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物体的移动可能取决于它的位置;我们也可能在心灵的活动中有同样的体验,我们可以感觉到思想和运动的永恒结合。所以,如果你仅仅注意观念,认为运动绝不可能产生思想,不同的位置绝不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和反思,那么你的推理未免太过草率了。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可能拥有这种体验,并且是确实拥有这种体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身处不同的位置会影响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这依靠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对此,我会回答,我们必须把灵魂的实体问题与思想的起因问题区分开来;倘若我们将后一个问题单独拿出来看,通过对比思想和运动这两个观念,我们会发现思想和运动互不相同;通过自己的经验,我们又会发现思想和运动是永恒结合的。而我们在考虑因果关系应用于物质的作用上时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永恒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运动可以且确实是思想和知觉产生的原因。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种情况是,除非大脑可以认知两个事物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否则没有任何事物是其他事物产生的原因。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所能发现的所有对象都是永恒结合的,因为这种联系而有了原因和结果。倘若我们选择第一种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宇宙中并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原因或产生的原则,甚至是上帝也不可以;因为我们对最高存在者的观念来源于一些特殊的印象,这些观念与其他存在的事物的观念没有任何可知觉的联系。你可能会说:"一个拥有无限能力者的观念与其意念所造成的结果之间存在必要且不可避免的联系。"对此我有两个回答:我们并不知晓一个拥有什么能力的人,遑论知晓一个拥有无限能力者是什么样;倘若为了改变这种说法,你想要去定义"能力",你就不得不提到"联系"。因此,当我们说对于拥有无限能力者的观念与对于其意愿所造成的结果的观念相互联系时,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说:意念与这些结果相联系的存在,其本身也与结果相联系;这就构成同样的命题,我们没法通过这一命题理解能力或联系的本质。其次,倘若我们假设,上帝是重大而有效的原则,补足其他一切缺失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对上帝极度的不敬和荒谬之中。如果我们因为感觉不到物质与运动或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就想依靠上帝来解释自然运作,认为物质本身不能传递运动,也不能产生思想;那么依照这样的理论,一旦物质似乎引起了什么东西,事实上都是上帝所赐;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所有的意志和知觉,因为这些知觉间互不关联,并且与我们假设存在但并不确定的灵魂实体也没有关联。神父马勒伯朗士和其他笛卡尔派主张用上帝来解释一切心灵活动,除却意志或意志中不那么重要的部分;显而易见,排除这个例外只是为了逃避信仰这种主张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如果除了具有明显且可感知的能力的事物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是活动的,那么思想的活动性就不可能比物质的活动性高;如果我们不得不因此而求助于神明,解释其因果关系,那么上帝便是我们所有行为的真正原因,不论行为是善与美,还是丑与恶。
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个两难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我们发现,人们单凭两个对象永恒结合,就认为它们具有因果关系。而既然任何互不矛盾的对象都可以永恒结合,又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说明(仅就事物的观念而言)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任何事物的原因或结果;这显然让唯物主义者占了上风。唯物主义者让物质成为全部事物的原因,而其反对者认为上帝才是事情的起因。
如果要做出最后的结论,那么一定是这样的:关于灵魂实体的问题是绝对晦涩难懂的;我们的某些知觉不占有空间,而某些知觉占有空间,因此它们不可能全部存在于同一个空间内;既然永恒的结合是因果关系的本质,那么就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一点理解来看,物质和运动往往可以看作引起思想的原因。
大家应该承认,哲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倘若迫使它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解释自己的结论,每当可能冒犯到一种特殊艺术或科学时,就要为自己辩护,那么这对哲学来说是一种侮辱。这就如同一个国王因对其臣民犯了叛国罪而受到控诉!只有当宗教似乎受到一丁点冒犯时,它才会觉得为自己辩护是有必要的,也是光荣的;因为宗教的权力与它自己的权力一样宝贵,事实上二者就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有人担心,我之前的论述有任何一点不利于宗教,那么我希望接下来的解释能够让他的担心烟消云散。人脑能想象出来的任何对象的运作与持续,任何一条先验的结论,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对象突然完全无用了,或是被消灭了;并且,凡是我们能想象出的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条明显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对于物质还是对于心灵来说,都是真实的;不论是对于一个占有空间的实体还是对于一个单纯而不占空间的对象来说,也同样千真万确。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形而上学对于灵魂非物质性的论证都同样无法令人信服;相反,道德的论证与由自然类比推导出的论证却拥有说服力。如果我的哲学理论没有为宗教增添什么说服力,但同时也没有减弱其影响力,一切都一如既往,那么我也至少可以满意了。
论人格的同一性
一些哲学家认为:
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自我;我们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也感觉到其存在的持久,而且我们确信--甚至超过相信其他任何一个论证--确信自我的完全同一性和单纯性。最强烈的感觉和激情不会消除我们这种自信,只会使我们更加确信,并且这种感觉和激情通过带给我们痛苦和愉悦,让我们思考这些感情如何影响自我。进一步证明自我的存在也并不能使它更加明白,因为不论我们采用何种论据,都不如我们自我存在的意识那般强烈。如果我们连这点都怀疑,那么我们便没什么可以确信的了。
可惜的是,所有这些直截了当的说法,都与本应可以用来维护它们的经验相反。我们并不像这里所说的那样拥有一种自我的观念。那么,我们的这一印象从何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陷入显而易见的矛盾与荒谬;但要想阐明自我的观念,我们又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真实的观念一定都来源于某个印象。但是自我或人格并不是任何一种印象,然而,我们认为,许许多多其他的印象和观念都与之相关。如果自我的观念来源于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印象一定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我们认为自我就是没有变化的。但没有什么印象是永恒不变的。痛苦和愉悦、伤心和快乐、激情和知觉,彼此交替,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因此,自我的观念不可能来源于其中任何一个或其他的印象。因此便没有这样的观念。
再者,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关于自我的假设,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所有特殊的知觉呢?所有的知觉都互不相同,独一无二,相互分离--它们可以分别考虑,独立存在,不用依靠其他任何事物。它们以何种方式归属于自我,并且与自我相联系呢?在我看来,每当我自省所谓的自我,我总会偶然发现一些特殊的感觉,如冷热、明暗、爱恨、痛楚或愉悦,诸如此类。我总能在自我中发现感觉,也只有感觉。当自我没有知觉之时,例如陷入沉睡的那一段时间内,我没有自我存在的意识,因而可以说我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死亡带走了我全部的知觉,如果我的身体凋零,我不能思考,不能感受,不能看,不能爱,也不能恨,那么我算是彻底消失了--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彻底消失。倘若有人在经过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后,认为自我有一个不同的概念,我不会再和他理论了。我不得不承认,他对于自我的认识也许和我一样,也是对的。他也许感知到单纯而持续的所谓自我,而我确信我没有与他同样的感知。
但撇开这种形而上学家不谈,我愿意认为,剩下的人类都只是不同知觉的集合,这些知觉快速交替,永久流动。我们的眼睛每在眼窝中转动一次,我们的知觉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思想甚至比视觉变化得更快;我们其他的感官都促成了知觉的变化,没有片刻的静止。我们的心灵如同一个舞台,不同的知觉相继出场:它们来回经过,悠然离场,混杂于无数的位置与场景之中。严格来说,灵魂在同一时间不具单纯性,在不同时候也不具同一性,不论我们在心里如何想象其单纯性和同一性。也就是说,在视觉上的蓝色和听觉上的哨声同时出现时,单纯统一的心灵能同时拥有这两种知觉,这种看法严格来说是错的;在某一时刻拥有某种知觉的心灵,与在另一时刻拥有另一种知觉的心灵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看法严格来说也是错的。我们不能被"舞台"这个比喻误导。接连不断出现的知觉构成心灵;而对于演出的场地或是构成这个地方的材料,我们还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是什么让我们赋予接连不断的知觉以一种同一性,认为我们一生都具有一种连续不变的存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我们认为与我们想象中的灵魂同一性,与其在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欲望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区分开来。前者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主题。为了详尽阐述,我们必须深挖这一问题:首先要解释我们认为属于植物和动物的同一性,因为这与自我或人类的同一性十分类似。
对于一个随着时间流逝而保持永久不变的对象,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观念。我们称这一观念为同一性。对于许多关系相近且持久存在的不同对象,我们也有一个清晰的观念;准确理解后,倘若这些对象无论如何都互不相关,那么它们就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多样性的例子,如同沙漏中的沙,这颗沙粒与那颗在零点一秒或是一微毫米之后落下的沙粒,都是不相同的;它们互不相同,简单来说,它们是两颗不同的沙粒,而非同一颗;而它们紧密相连的事实(空间上、时间上,以及实质上都是相似的)也不会对此产生任何作用。它们互不相同,如同泰姬陵和美国大峡谷的差别那样明显。尽管同一性和相关对象的连续性这两个观念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我们在通常的思维方式中,仍然喜欢把它们混淆在一起,认为这两个观念是一样的。现在我来说明,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这种混淆。以下有两种思维活动:
(1)思考一连串的相关对象
(2)思考一个永恒不变的对象
这两种思维活动虽然互不相同,而且涉及不同的想象活动,但它们感觉上是一样的。第一种思维活动并不会比第二种更加耗费脑力:在第一种思维活动中,对象之间的关系帮助思维轻松地从一个对象转移到下一个对象,使得整个思考过程顺畅无阻,如同在第二种思维活动中思考一个永恒不变的对象一样。其相似之处就是混淆的原因,使得我们错误地用(2)中同一性的概念代替了(1)中相关对象的观念。在思考连续的相关对象时,即使某一瞬间我们认为它是可变、间断的,但下一瞬间我们就会错误地认为它是一个单独、同一、不变、不间断的事物。这一点使得解释更加完整。正因为上面提到的两种思维活动有相似之处,我们才有很大的概率会犯下错误,甚至根本认识不到我们正在犯错;即使我们不断纠正自己采用更准确的哲学思维思考,我们还是无法持久保持,而是再一次犯下错误。为了不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谬误屈服,并且勇敢地断言,这些不同的相关对象虽然间断且变化多端,但其实是相同的。为了将我们自己的荒唐言论正当化,我们时常虚构某个不可理解的新原则,将对象联系起来,以消除间断和变化。我们的感知是间断的--对象之间存有间隙--我们将其掩饰起来,假装它们是连续存在的;它们变化时,我们又想出灵魂、自我和实体这些永远不变的概念,借此来掩饰变化。即使在我们不去虚构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混淆同一性和相关性,我们很有可能想象,除了各部分的联系之外,还有某种未知而神秘的东西将各部分联系起来;我想,我们赋予植物以同一性,就是一个例子。即使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甚至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也无法找到任何永恒持续的东西来证明我们关于同一性的概念,我们还是感到很有可能将这些观念相互混淆。
因此,关于同一性的争论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争论。因为,当我们错误地认为变化或间断的对象具有同一性时,我们不仅表达错了,而且还陷入虚构,陷入一种错误的思想,要么虚构一些不变而连续的对象,要么虚构某种神秘而费解的联系。要说服一个态度公正的人相信这一点,我们只须让他通过自己的日常经验意识到,当他认为变化或间断的对象持续不变时,它们事实上是由连续的部分组成的,因为类似、相近或因果关系而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连续的变化显然符合多样的观念,因此我们赋予其同一性只能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是,思维从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相关部分的思维活动,与我们思考一个不变事物的思维活动相似。那么,我须要重点解释的就是,尽管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对象具有连续、不变的性质,而却要赋予其同一性,我们其实真正要谈的不是一个独立的对象,而是连续的相关对象。
首先,假设我们面前有一团物质,它的各个部分都是相邻且相连的;显然,只要它还是由这些部分组成,即使这些部分在其中有什么连续的运动变化,我们都认为这团物质具有同一性。现在我们假设,这团物质中增加或减少了某个极小、不起眼的部分。严格来说,这团物质不再和之前的那团物质一样了;然而我们不习惯思考得如此精确,由于差别极其细微,因此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团物质还和之前的"一模一样"。我们的思维是如此轻而易举地从变化前的对象转移到变化后的对象,以至于我们忽视了这种思维转移;并且,这还让我们误以为仍在观察同一个对象,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一现象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一团物质中重大部分的改变破坏了整体的同一性,即让我们不愿承认它还是与之前相同的物质,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重大并不取决于这个部分的实际大小,而取决于这个部分占整体的比例。倘若一个星球增加或减少了一座山,我们仍可以说这个星球和之前"相同",但有些物体只要有几英寸的改变就可以破坏其同一性。唯一的解释就是,对象不是依照其实际大小,而是依照它们彼此之间的比例来阻断心灵活动的连续性的;由于这种阻断使得对象不再"相同",那么一定是不间断的思维过程构成了那种不完全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不间断的思维过程让我们认为,那些严格意义上不同的对象是"相同"的。
另一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某个部分的重大改变破坏了物质的同一性,但倘若这个改变是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的,那么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概率会认为这个改变破坏了同一性。这是因为思维在跟随物体连续的变化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观察这一秒钟的状态,转移到观察另一秒钟的状态,并且从来意识不到转移过程中有任何中断。
但是,不论变化发生得如何小心翼翼、如何不知不觉,尽管每一次的变化只占整体的一小部分,但最终这些微小的变化加起来成为重大的变化时,我们很难毫不犹豫地说这样一个不同的对象具有同一性。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想象更进一步,将同一性赋予完全不同的物质。这个方法就是将各个部分通过共同的终点或目标联系起来。一艘船经过数次修缮,即使材料已经大不相同,人们仍然认为它和之前"相同"。船的各个部分不论如何变化,仍然拥有共同的功用;这就让想象轻而易举地从修缮前的船转移到修缮后的船。
倘若我们认为各个部分在所有活动中,因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互为因果,那么上述情形就更加显著了。轮船的例子与这种情形不同,但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属于这种情形:各个部分不仅拥有共同的目的,而且它们为了进一步达到那个目的,相互依靠、相互联系。这种关系的作用就是,尽管几年后动物和植物都完全不同,其形状、大小和实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认为其具有同一性。一棵小橡树,长成一棵巨大的橡树之后,仍然是同一棵树,尽管没有一个物质分子或部分的形状与以前相同。一个婴儿长大成人,尽管时胖时瘦,也没有改变他的同一性。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个现象是,虽然我们一般可以准确地分辨出数量的同一性和类别的同一性,但偶尔我们还是会混淆,在思考和推理时用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例如,一个人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那是"同一种声音"。显而易见,声音只有类别的同一性或类似关系,并没有数量的同一性,只有发出声音的原因是相同的。与此相似,一座砖石建成的老教堂倒塌之后,教区的居民又用沙石按照现代建筑风格建了一座"同样的教堂"。这座教堂的形式与材料都与从前不同了;除了与教区居民的关系以外,这座教堂没有一点是和之前相同的;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称其"相同"了。在声音与教堂的这些例子中,第一个对象在第二个对象出现之前可以说已经彻底消失了。这防止了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不同和多样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同一时间面对两种声音(或是两座教堂),然后思考"这是第一个,那是第二个";这让我们更加毫不犹豫地称其"相同"。
第二个现象是,尽管我们一般只在相关事物逐渐变化、部分变化时才赋予其同一性,但是对于那些本身就变化无常的对象,即使发生突变我们也认为它们还是"相同"的。例如,河流各部分本来就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因此即使它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完全变化,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若干世纪中是"同一条"河流。任何东西的自然而本来状态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而凡是可以预测出来的都不如不同寻常来得印象深刻、至关重要。在想象中,前者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都比出乎意料的微小变化更加微不足道;因此前者变化对于思维的连续性破坏力更弱,对同一性的影响也就更小。
现在我继续解释人格同一性的本质,这已经成为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上面的推理方法成功解释了动植物、船和房屋的同一性,也解释了所有变化的复合物体,包括自然物体和人工物体的同一性,现在我们继续用其解释人格的同一性。人格的同一性是我们虚构的;就像我们赋予动物和植物的同一性一样。因此,它们的来源一定相同,并且一定来源于对于相似对象的想象过程。
这一论证可以完全说服我,但是倘若你仍然不相信,你可以考虑以下更加严密、直接的论证。虽然我们赋予人类心灵以同一性,但显而易见,不论我们想象它如何完美,都不可能让许多不同的知觉失去其重要的特质,然后将它们合为一体。加入人类心灵组织的每一种不同的知觉,都与其他知觉(不论是否同时出现)相互区别、相互分离。而我们假设所有这些知觉都因为同一性而结合,我们说这些知觉都是一个人的知觉,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关于人格的问题。同一性是把我们不同的知觉本身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纽带,还是仅仅在我们的幻想中将不同知觉的观念联系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一个人的同一性时,我们是观察到这个人所感知的知觉之间有真实的联结,还是仅仅是我们对于那些知觉的观念之间有联结?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之前所证明的,那么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即我们从未在对象间发现任何联系,甚至在严格审视下,因果关系也只是习惯性观念的联系。显然,这意味着同一性从未真实地属于不同的知觉,也从未将其统一起来;同一性只是我们考虑不同知觉时、因它们相互统一而赋予它们的一种性质。现在,只有我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性质可以在想象中统一各种观念。它们是观念世界中的结合原则;没有这三种性质,每一个不同的对象在心灵与思想中都是分离的,并且看上去彼此无关,就像与那些完全不同、距离极远的对象无关一样。因此同一性必然依靠相似关系、相近关系和因果关系中的某种。这些关系的本质就是让观念可以顺利地相互关联;因此,人格同一性的概念一定如同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完全是由于相关观念间的连续而流畅的思想运动而产生的。
现在仅剩下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思考那些被我们看作为构成了心灵或思想人格的连续知觉时,到底是哪一种关系让我们产生了不间断的思想运动?显然,相近关系在这里没什么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相似关系和因果关系。
我们首先从相似关系谈起。倘若有人永远记得他过去的大部分知觉,那么尽管他的知觉变化无常,但这对于他掌握自己知觉的某些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记忆无非就是一个工具,我们借其唤起对从前知觉的印象,而某物的印象一定与某物相似。因此,每一份记忆都有知觉,这知觉与他之前所拥有的知觉类似;并且在思维过程中,这些时常出现的类似知觉让想象在各个环节中移动得更加顺畅,使得整个过程如同一个对象的连续。在这种情形下,记忆不仅展现出同一性,而且产生相似的知觉,有助于创造同一性。这一段前面所阐释的,不仅适用于考虑自己人格的同一性,也适用于讨论他人人格的同一性。
因果关系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人类的真正观念是一个不同知觉为因果关系所联系的系统观念,这些不同的知觉相互产生、相互消灭、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我们的印象引起相应的观念,相关观念又反过来产生其他的印象。一个思想赶走另一个思想,紧接着又被第三个思想赶走。在这一方面,灵魂非常像一个共和国或联合体,在这个共和国中,成员被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结合起来;他们随后又生出其他成员,这些成员又继续通过各部分不停的变化维持这个共和国持续存在。同一个共和国不仅可能替换成员,也会更新其法律和制度;同样,同一个人不仅他的性格和性情会发生变化,其印象和观念也会不断更新。不论他经历怎样的变化,他的各个部分依然为因果关系所联结。我们的情感,通过让某些知觉影响其他不同时间点的知觉,最终同我们的印象和观念一样,也促成了人格的同一性。当我们现在思虑到过去或未来的苦乐,就会出现上述的情形。
记忆应该是人格同一性的来源,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记忆,我们不会记得漫长而持续的一系列知觉。如果我们没有记忆,我们永远不会有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因而也不会有构成自我和人格的因果观念。但是,我们一旦从记忆中发现了因果关系的概念,我们就会将这些原因和人格的同一性扩展到记忆之外,包括我们已经完全遗忘而只是一般假设存在的时间、情景和行为。我们真正记得的过去行为还有多少?例如谁可以告诉我,他在1715年1月1日、1719年3月11日和1733年8月3日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他是否会因为忘了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而说现在的自己和那时的自己不同了,从而否认了人格同一性最显著的概念呢?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记忆展现了不同知觉的因果关系,因此与其说记忆创造了人格同一性,不如说它展现了人格同一性。而那些认为人格同一性完全由记忆引起的人,必须解释我们是如何将人格扩展到记忆之外的。
这个学说的全部主张引领我们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关于人格同一性的任何细致而微妙的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应将其看作语法问题而非哲学问题。同一性取决于观念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借思维顺畅的移动引起了同一性。但是关系有深浅之分,移动的顺畅程度便取决于此;因此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来判断对象何时具有"同一性",何时又失去了"同一性"。正因为同一性的存在取决于关系的深浅程度,所以就一定存在临界情况,就像秃顶和高度等等。关于相关对象的同一性,一切争论都仅仅是空谈,实际上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只是因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虚构或想象出的结合原则罢了。
关于人类对于同一性的概念的起源和不确定性,我的论述无须改动,也可以适用于单纯性这一概念,即一个对象不可分。一个由不同的相关部分共同组成的对象,在认知上和一个单纯不可分的对象是一样的,无须付出较多的思考。由于二者思考起来是一样的,我们便认为前者是单纯的,并且我们创造出一个结合原则以证明其单纯性,并将这个结合原则视作一个对象的不同部分和性质的中心。
全名大卫·休谟(DavidHume),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怀疑论者,不可知论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只承认感觉经验的真实性,质疑一件事伴随另一件事而来、两者间必要有关联的因果论。主张所有人类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联结"和"实际的真相"。在西方哲学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相关作品:《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
转自:凤凰网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