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地方。每当广播中电视里有人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远走高飞”,不一会,便到达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新集镇朱营村陈庄组。
在这里,我站在宽敞的环河沥青观光公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举目远眺,两座从连云港市架设过来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显示,这里的一切都处在一派繁忙景象之中;再环顾四周,一边是清清流淌的滁河水,一边是南京六合人工水面养殖示范基地,两边水面上都漂浮着一阵阵飞来飞去的野水鸭、白天鹅、鸳鸯鸟,他们共同描绘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壮美蓝图……看着这些改革开放农村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我的心情真的有些陶醉了。我在反问自己:若大个世界,为什么偏偏要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呢?也许,这就是人的一种本性,一种本能的反应,一种人皆有之的归宿感!不论家乡过去是穷是富,也不论家乡现在是如何步入新时代的,我对家乡的思念是厚爱有加的,是至死不移的。

1991年2月,王光英、王光美在北京师范大学接受李德金(左一)采访

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

李德金(后排右一)采访“两会”港澳委员座谈会
儿时家乡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像“人之初,性本善”一样,是带有传承性的。我不管走到哪里,走多远,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记忆犹新的,尤其是在工作、生活上遇到不便的时候,这种记忆会像电影胶片一样,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他在鼓舞我激励我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去拥抱新的人生。这种来自家乡的“力量”,可以说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曾记否,在遥远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是靠胡萝卜获得新生的。从那时起,我就对家乡产生了一种感恩之情。因为当年,如果沒有家乡的沙土地,适宜种胡萝卜的传统习惯,我可能早就到西天“取经”去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家乡的记忆才越来越深刻。在十年“文革”中,我茁壮成长,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又回乡务农几年,用两个肩膀与农民兄弟一起挑出两条新河——三岔湾河与程桥河,为家乡兴修水利参与开凿了一条小河,架起了一座电灌系统……正当我要立志务农的关键时刻,大学开始招生了,又勾起我读书的欲望。1975年10月,经过推荐加考试,我从原新集公社2000多名报考者中获胜,成为原全六合县两名上大学名额中的一员。当时,前来接收学生的上海招生办老师在面试中问我:上海有两所高校一个是复旦大学,一个是海运学院,您希望上哪一所学校?我说老师您定!结果很快我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录取了。在上海3年,我总是以家乡那种吃苦耐劳精神为傲,并以这种精神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实现了在家乡早有的梦想——如果能够上大学就好了;上了大学,又再想,如果能够到首都北京工作就好了,如果能够当上一名人民日报记者那就更好了!结果,是老天作美,我的梦想都一一变成现实。1978年6月,我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在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干了1年,我又加入到了中央国家机关援藏干部的行列。记得那是1979年6月,我和群工部阙邦火、程先妮夫妇从北京站乘火车到甘肃柳源站下车,与兄弟单位援藏干部会合,一起参观了“月牙泉”、敦煌石窟等名胜古迹。随后,我们便乘坐着一辆辆公共汽车,踏上了援藏之路——翻过海拔50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跨过“死亡之地”沱沱河(因为此处地势险峻海拔高,又气候多变,常有人在这儿体力不支而患上感冒,由于离前方接待站很远,患者不可能得到及时救治,就会迅速由肺炎转为肺气肿……还有人到达此处会假死,据说,有一天,一个新兵在此处因假死是改乘飞机入藏的),汽车行驶的路,由于正在改建,到处泥泞不堪,到处坑坑洼洼,落差很大。汽车在艰难前进中,一时被高高抛起,一时又被重重摔下,左右摇幌、上下颠簸,使我这个最年轻坐在最后一排座上的人,头脚好像两不着地,五脏六腑被颠得快要崩出来似的。一路上,行驶的汽车车轮有时掉入沿途泥泞的车辙里爬不上来,还要人下来推;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辆辆大卡车一个又一个小汽车,不是摔在茫茫戈壁之中的盐碱公路(路面沥青被阳光曝晒容易崩裂也容易被滚滚沙尘暴掩埋)旁,就是迭落到弯道拐过来拐过去的深山峪谷里;一路上,不知道汽车拐了多少弯,翻越了多少高山峻嶺,好在经过6天的日夜兼程,在几个简易通铺接待站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拉萨西藏日报社。现在回想起这些,真是有点触目惊心,后怕不已。不过,当年,对我这个刚进城的农村青年来说,什么都感到新鲜,有一股敢想敢试敢做的拚博劲头。在西藏日报社,阙邦火被分配到汉文版的农村组工作,我被分配到汉文版的政法组工作,与后来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卢小飞是同事。在西藏3年,我结识了原人民日报社援藏干部——西藏日报社的周美生、毕月华、杜淑颖夫妇以及后来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吴长生同志。他们有的已援藏20年左右,为我做出了学习的榜样。因此,在西藏日报社,我与藏族同胞和睦相处,克服了高原反应——每天虽然头重脚轻,气喘吁吁,心跳加速,肺呼量增大,但仍坚持像老援藏干部学习,像藏族同胞看齐,尽量摆脱高原缺氧造成的重重困难,努力改变自已,沒多久,就适应了高原“吃辣子”、喝酥油茶、住低矮土坯房的生活习惯,也适应了高原骑自行车采访的工作方式。在拉萨,我采访过藏族带领农民致富的老阿妈,她相当朴实热情,见我是汉族人,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开罐头肉,一边做米饭,一边赶制酥油茶;在林芝地区,我采访过北京援藏教师,他带我认识了因产麝香而成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香獐子以及藏羚羊;在藏北羊八井,为采访地热建设成就,我和老同事一块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一周,领略了美丽的高原雪景风光;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我采访过自治区原副主席天宝……通过这些采访活动和所见所闻,使我深深感到“藏汉一家亲,谁也离不开谁”这句话,应该成为加强民族团结的至理名言,成为一条颠覆不破的生活真理!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胡跃邦视察西藏后,提出从西藏调回一批援藏干部的时候,藏族同胞依依不舍,有很多人拉着援藏干部的手痛哭流渧,这里面有些属于感情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工作上的难舍难分,尤其是在技术层面更是这样。当然,在西藏日报社汉文版,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干编辑记者这一行,成天与藏族同胞打交道,也离不开像藏族同胞学习取经,离不开像身边援藏几十年的老同事学习,是他们那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援藏精神和我的农村吃苦耐劳精神一起,成就了我的援藏理想,使我有机会认识了世界屋脊这片神奇的土地,与藏族同胞结成一片,使西藏拉萨继北京之后成为我的第三故乡。

1999年3月,在“两会”期间,李德金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合影

李德金(右二)与人民日报“两会”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留念

李德金(左一)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两会”上合影
原来,我这个拥有农村“哪里黄土不埋人”倔脾气的人,是准备在西藏干一辈子工作的。不料,1981年,援藏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又响应中央号召,同周美生等一样,先后被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198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我到政法部任编辑记者。由于海外版人员编制少,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编采合一工作流程,再加上政法版是新闻版,要值夜班,一般情况下,每天值夜班的是一个主编带一个编辑上。而我在值夜班的时候,因主编在忙于编社外杂志,所以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编稿、送车间打字、画版样、出相纸、贴版样、复印出样送值夜班主编和总编审改、改样送车间改后再出相纸贴版复印出样、再送审后如沒有大改动即可签字付印或改后付印。前后从晚上8时上夜班,通常要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下班。有时,从位于朝阳区小庄的报社回宣武区虎坊桥家的路上,困得累得真想放倒手中的自行车,在路边睡一觉再回家。即使是这般模样的我,进家躺一会,送完孩子上托儿所,又骑着自行车前往所负责联系报道的单位——或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或中共中央统战部或各民主党派中央或全国工商联或国家民委或公安部或民政部或中国残联或全国妇联或国家知识产权局采访去了。每年撰写消息、通讯、特写、专访、深度报道等约10万字,有不少新闻作品先后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民政部、国家民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好新闻奖。在人民日报首次开展的好新闻评选中,我也有一篇榜上有名,并连续两年被评为人民日报社先进工作者。在中国残联、中国记协组织的首届奋发文明进步新闻奖评选时,我还获得了一座“维纳斯雕像金奖”。除此之外,在海外版值夜班近20年里,我曾随远望号测量船赴南太平洋测量卫星发射,往返航海半个月,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万吨巨轮就像一叶扁舟,一阵阵巨浪袭来,扑天盖地,好像要吞噬整个船,在返航时,远望号的部分设备已经受损,但仍顺利回到出发地江阴,至此,我也圆满成了这次报道任务;我曾参加中宣部、中国记协等单位共同组织的以“了觧国情体验生活”为目的中央新闻单位百名名编辑名记者江西老区行活动,在一周时间里,除了参观瞻仰井冈山、瑞金多处革命遗址外,还到赣州市犹江林场与务林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两天,写了“记者感言”《老区河山壮哉美哉》等六七篇文章和自拍的多幅图片分别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中国记协网刊登,并被多家网站转载,为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增添了新鲜内容;我曾两度被国务院610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抽调去撰写有关文章和有关文件,工作结束时,对方都致信人民日报社表示感谢并对我个人工作给予表扬;我曾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投身到新闻媒体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中去,在中国四大产棉区之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采访了棉花套种土豆、辣椒实施科学种田为棉农增产增收的新方法新经验,文章《冀南棉海地生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版《记者走基层》专栏刊出后,受到广大棉农的称赞;我曾多次参加人民日报社组织的全国“两会”报道工作,写过不少有份量有影响的宣传报道稿件,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下了深厚友谊。由于我是全国“两会”的“老运动员”,还与中央电视台一起主持过现场采访节目,参加过不少“两会”记者会,也提问过一些问题。在平时采访报道中,我多次采访过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其中,也包括香港的霍英东先生、澳门的马万祺先生。有一年,民进中央在香山饭店召开主席扩大会议,只邀请我一个记者参会开展宣传报道工作,中午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一块共进午餐,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是我多年积极从事民主党派宣传报道工作,与民主党派成为好朋友带来的结果,也是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光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残联组织召开了一次小型残疾人座谈会,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座谈会上与残疾人亲切交谈,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作为一名记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报道工作。在以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的常委会议期间,我经常聆听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所作的精彩报告和讲话。这些领导人都非常平易近人。有一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中小休的时候,李鹏委员长与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楼道交谈,我有事刚好从他们身边走过,但他们仍然面带笑容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还有一次,我从人民大会堂参加完会议要乘电梯下楼,一按电梯按钮门开了,里面恰巧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他的秘书,我立即收回迈出要上电梯的脚,李岚清和他的秘书马上示意叫我上电梯。通过这两件事,使我体会到中国领导人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是靠领导魅力、工作魅力、人格魅力而赢得的。在全国政协成立45周年之际,李瑞环主席为此举行了一次小型庆祝招待会,我和新华社记者应邀出席。在席间,我向李瑞环主席敬酒热烈祝贺全国政协成立45周年,李主席欣然站起身来举杯表示欢迎和致谢!

图为在全国政协成立45周年之际李德金(右一)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左一)敬酒表示祝贺!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欣然为九界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开幕题诗祝贺
2015年3月,在退休3周年之际,我在生我养我的第一故乡回忆从事新闻工作30几年的不平凡经历,在人民日报这块大牌子的呵护下,一定会涌现出许多精彩的瞬间,但也会遇到不少惊险的瞬间。1989年初夏,我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去采访,行至报社西门对面公路左拐处不远的地方,被一辆从这个方向突然高速窜出的小轿车撞出13.5米,这是车祸发生时报社保卫处派人去事故现场丈量的结果。当时肇事司机在场,他看见我撞碎车前挡风玻璃又被抛出去很远,认为我一定死了,吓得直打哆嗦。而我呢,在抛出一刹那间,在脑海里闪过的念头也是这次完了。确实,当我矗立落地后又蹲下的当儿,我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庆幸的是,不一会儿,我又恢复了知觉并站起身来,只见司机一边从上衣口袋掏出驾驶本给我看,一边说责任全在他,事故是由他高速急拐弯(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大约时速有八九十迈)又有景观松树障眼造成的,表示要负全责。后来,他看我被撞得这么严重,不但未死好像身体也沒有什么大碍,又找人出来说情要求私了,结果是因肇事者耍无赖而使事故处理不了了之。其实,我那次大难不死,多亏的是我骑的28自行车“人高马大”,为我挡了车轮并把我挑起撞碎汽车挡风玻璃后再抛出去的,如果那次沒有自行车挡一关,当时我肯定必死无疑。在北京,这是我发生的一次性命攸关的大事故。在外地,我也同样遇到过多次要命的大事故。一次是赴重庆钱江地区采访,晚上小轿车行驶到一条左边是陡峭深塘的公路上突然右边前轮飞出去了,小轿车依靠三个轮子迭迭撞撞跑了几米远,倒在了公路右边,如果往左边倒,就会掉进不知有多深的塘里,不摔死也会被淹死;一次是在一个叫“鬼门关”的乡村公路上,司机不小心,把前面一个车轮子掉进路中间的深土坑里,由于速度较快,车马上急拐掉头处于侧翻又不倒之中,待惊险一幕过后,它又很快正过身来停在公路上。当时站在一旁的农民看到这一切,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以前经常有人到这儿一出事故,就是车毁人亡,而你们是个例外,应该是祖上积德多了吧!还有两次是乘飞机遇到有惊无险。一次是飞机降落时轮子放不下来,在空中忙乎半天才降落;另一次是飞机降落太快,后部轮子差点刮在机场护栏上,是驾驶员反应快及时拉高才避免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
忆往昔,还看今朝。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时间在家乡忆忆往事,对比对比得失,以求心里的平衡,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想,这就是我提笔写这篇小文的初衷!但愿家乡的记忆常忆常新,永远不会忘记……
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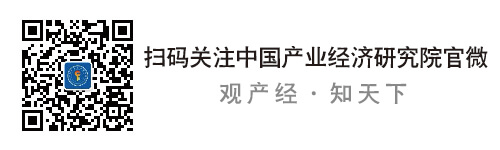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