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完全不似《战争与和平》里的死人样。因此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泥淖。《安娜·卡列尼娜》完美体现了托尔斯泰重剑无锋的珠圆玉润之风格,是一本最优雅的小说,因为它最能够体现贵族尊严的光辉和人类的道德自省。相比之下,《高老头》是菜市场人物志;《包法利夫人》显得寡廉鲜耻;《尤利西斯》过于广博而远离尘世;《战争与和平》是木偶的小说:所有人,包括灵光一现的娜塔莎,都是托尔斯泰的说教木偶。
《安娜·卡列尼娜》的魅力是不朽的,如果去除结尾处列文絮絮叨叨的琐碎教诲,它则是一块浑圆无瑕的玉石,经得起文本和指涉的多重推敲。
安娜·阿卡德耶芙娜·卡列尼娜,看似享有一切,其实却什么都没有。她历尽曲折与成规的束缚斗争,终于拥有了渥伦斯基的爱,却在猜忌和自省中将它毁灭了。安娜的生活是照出彼得堡上流社会之优雅的镜子,却同时又只剩下强烈情感驱动本身、空虚到极点。
起先,她拥有一个貌似幸福的家庭,自己却毫无获得感。卡列宁与她相敬相依,却并不懂她。哪怕卡列宁娶了一座大理石雕,他也一样会嘘寒问暖、顾虑周全:此时的安娜没有情感生活,她的感情被压抑。后来,安娜与渥伦斯基走到一起,却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处境带来的痛苦,她尝试历史、地理、建筑、绘画,其学识一度让渥伦斯基“惊讶”,然而她为的却是满足渥伦斯基;她领养了英国女孩,也只是出于心灵排遣的需要,“像吗啡一样”。
安娜一直在非常态的生活之边缘游走,因为她的生活不被认可。她和渥伦斯基的guilty love造成了这一切,自从她与渥伦斯基前往欧洲,她就已经被彼得堡上流社会所不容,被所有的朋友所抛弃。
彼得堡的圈子是一个“系统”,是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生活的系统。既然所有人都身处这个系统之中,就不能以对错之分划定人格。这个圈子又是权力话语体系,也许在彼得一世时代就已经存在着;这个圈子经历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这个圈子遗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年代,不管其中风气如何,它们确实都已经固定下来,成为不可质疑的规矩。
渥伦斯基就生长在这个系统之中,他身边的亚希文就是圈子里人物的常态:纵酒、赌博、赛马、“正派”、风流韵事。当代人逾越世纪鸿沟当然可以看出帝俄贵族的腐败堕落;扎根在系统里的帝俄贵族们却生来就处于道德崩坏的悲剧之中,他们的伦理观天生带有堕落的印记,终生不能从泥淖中摆脱。这是他们的悲剧。
因为这个系统,渥伦斯基面对凯蒂才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沙俄底层农民保守拘谨,而上流社会的糜烂奢侈、道德失序则是常态。只要男男女女把感情当作游戏,并不付出真心,这就成为一种谈资,也许还能增进魅力;可要是付出真心实意的爱,它就成了枷锁和罪恶。
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是陛下宠臣;她自己地位尊荣,“在彼得堡有三个圈子”,是彼得堡上流社会最美丽的贵妇人。可是她的眼中有一种被压抑的生气,那也是与渥伦斯基的惊鸿对视中被他捕捉到的东西。
卡列宁,我最同情的人,一位工作勤勉、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一位为人所称道的朋友,一位为家人铺路的丈夫,一位品味欠缺但努力过之的饱学之士,他的勤勉并不为追求虚荣,也不出于打击政敌、贪图功名的目的,而确实是受内在伦理观的驱动:正直、严谨,面对奥勃朗斯基的升迁请求而拒绝,却正应了那句老话“一位她不爱的男人,做任何事都是可憎的”。
渥伦斯基一度耻笑他,可渥伦斯基才是对不起他的那个人;安娜,因自己获得感的缺失而痛恨他,说他是“机器”,不时想“他的耳朵为什么那样大”——甚至这也能招来她的憎恶——然而她内心深处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因为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还希望世界谅解自己发出和遭受的不公平。
然后呢?卡列宁面对这件不名誉的事情带来的羞辱,面对安娜的指责和社交界对他的抛弃,面对一对欺骗她的男女,选择了宽恕,意识到这种高尚带来的喜悦,且不是出于自我感动。
现代社会中,有多少人敢渴望一场有爱情的婚姻呢?若是这样,那么卡列宁必定是当今时代一位理想的丈夫。卡列宁崇高的社会地位、大笔财富、能给妻子带来的交际圈子和尊重给予他世俗的成功标准。可是他却不能给安娜带来爱。
卡列宁按照书本和教育中的死板模型来生活,用知识构筑起自己生活的牢笼,把生活隔绝在工作之外,从没有勇气踏出去。对待儿子谢里沙,他甚至都按照书本的模型来模仿、来机械地构筑,“父亲跟他说话时总是像对某个他想象出来的、一个书本里的那种男孩子说话”;毋如说,谢里沙对卡列宁而言像是一个抽象概念。对比列文,在孩子降生时表露出鲜活的恐惧、感动、喜悦和心灵的极大震撼,卡列宁的确不是一位好的精神伴侣。
因为他迟钝的感知能力,当他听闻了风言风语、目睹了赛马的一幕、听了安娜的坦白,他并未崩溃,而是第一时间选择逃避。他自己“生活在一座桥上”,但是突然“桥上的木板消失了”,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他卡列宁,在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竟然选择忘记这件事,“不去想她”。他甚至不敢想自己的不幸,还是安娜的账单被送来时才被迫意识到悲剧的诞生。卡列宁不光是不想要真正的生活,也不敢看清真正的生活。卡列宁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安娜这样一个灵动强健的女人怎么可能不觉得压抑呢?
卡列宁是一个想要下定决心,却一直缺乏决心的人。这是放任;但同时又是宽容。进家门时他还在下定决心杀死安娜,可一见到她虚弱汗涔的脸,见到濒死的真诚,心冰又彻底融化;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私生女,他视若己出,“生活重心都在小女儿身上”;他本不信教,甚至对上帝的作用也要用工具理性权衡一番,最终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神圣感召,用自己的不幸来涤荡灵魂。
我不能把这归因于情感干枯;卡列宁虽然缺乏共情,没有丝毫的“经验生活”,但绝不虚伪。
可是卡列宁值得责备吗?必然是无可责备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做了自己应做的事。他把自己的自尊踩在脚下,成全了安娜的幸福,同意了她离婚的请求,甚至允许她把谢里沙也带走。如果小说开篇的卡列宁给人一种僵尸一般的官僚、伪善者、不信教者的印象,那结尾处的卡列宁才是他的本原:缺乏感知但善良的基督徒。
虽然他骨鲠,冷漠,可对待家人称得上爱护,对待事业称得上尽责。卡列宁是一个善良的人。
渥伦斯基向来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曾经无数次想象与卡列宁决斗的场面,骂卡列宁“是个懦夫”、“虚伪”,却被卡列宁握着手,用高尚、宽容和博爱彻底折服,殆尽了心中最后一丝不敬,顿时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对渥伦斯基来说,此前的人生中怕是从来没有这种耻感出现过。他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因自身的才学和人情世故的手腕而获得尊重和认可,被公认拥有远大的前程;因为系统的糜烂和道德失序,渥伦斯基用系统里寻常的玩世不恭对待他人,按照系统外的眼光看来“欺骗了”以凯蒂为代表的许多女人,按照系统中的眼光看来却“增添了几分魅力”。
然而,渥伦斯基,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第一次突破了系统的茧;他对安娜的爱是热烈而执着的,也是忠实和真诚的。
渥伦斯基抱负远大,在军团里享受着快乐和满足,直到他遇到安娜。车站里那个笑得充满活力的夫人改变了他的命运。渥伦斯基起先稍稍逾越了雷池,他和安娜的故事果然“增添了”他的魅力,他的母亲、哥哥也颇为赞许;后来他放弃了远大的前程,干脆和安娜私奔去了国外,彼得堡一片哗然,这才不得不对渥伦斯基和安娜产生的真正的爱情有所反应。
渥伦斯基的爱是坚韧的。如果他面对安娜嫉妒、猜忌、暴怒的行为选择逃避,那大可把他的追求归结为欲望的驱使;可他面对安娜反复的(真的数不清多少次)对假想敌的嫉妒、对他不忠的怀疑、无端的暴怒、对他事业的阻挠、对他的讽刺,仍然不离不弃,为她担惊受怕、流泪痛苦,虽然几次处在绷断弦的边缘却依然强烈地感到对安娜的依恋和爱,被安娜的眼泪“吓坏了”,面对安娜的任性,虽因自尊而表面冷漠、行动上却处处包容爱护,这就不是欲望和轻浮,而是爱。
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激情澎湃。安娜死了,可她是胜利者;凯蒂婚姻幸福美满,安稳度日,选择了最稳妥的道路,将在烛火旁的瞌睡中和儿孙的环绕中度过一生,平和而快乐,却是彻底地失败了。凯蒂是一个聪明人,但不是安娜那样舍生忘死的聪明。凯蒂看清了自己的勇气追求不了那样真实的爱情,所以她学着姐姐们的模样,嫁给了一个平凡人,嫁给了一个安稳体面的生活。
凯蒂的聪明是知足,是经历了成长的摧残和初恋的欺骗后的降低期待,因此面对列文日记的坦白而不紧追不舍,面对列文遇见安娜后的心神荡漾而不气急败坏。她活得平和且聪明,又并未丧失自我,深得瓦莲卡人生智慧的内核,再也不畏惧生活的击打。这就是凯蒂,一个被生活改造成女人的少女,有着无可指摘的快乐和良善,却绝不是人们最渴望成为的那类人。凯蒂是真实和热烈过后退而求其次的最优解,进一步就是烟花般爆裂的安娜,退一步就是懦弱不自知的多莉。
凯蒂的姐姐多莉一辈子都在忍受奥勃朗斯基的挥霍、出轨、欺骗,而她软弱、平庸,也和生活中大多数软弱、平庸的人一样善良、朴实。奥勃朗斯基,一个最不学无术的油条,他的种种出轨、赌博、裙带关系皆令人作呕,却独独有一副令人喜爱的好脾气;他的后悔可爱到令人无法动怒,他的笑容甚至治愈了倍感痛苦的卡列宁。他懂得如何获得快乐,如何利用“系统”的规矩而不逾越它,他在这个世界中凭借性格的善良为他人着想、为自己着想,是一位无比成功的庸人,一位甘愿含着奶头乐过活的寄生虫,却也是一位与世无争的好人。“任何人见了他这副笑容,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列文,完全不应似传统中对他评价的那般真实、清醒。我非常不喜欢他。他追求生活之真实的行为值得尊敬,他受困于执行力和受阻于深入思考中的碰壁的缺点令人叹息。他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诚实的待人之道,却不能够控制一时情绪带来的极端乐观或悲观的观点,一时认为所有人都糟糕至极,一时又能在喜悦的驱使下无原则地对所有人和善宽容。
列文前期不成熟的个人主义倾向是今日社会乱象的起因之一,“可这与我的利益又有什么关系呢”读来令人发笑。他不赞同斯维亚兹斯基的理论与生活脱节的生活方式,每当谈话撕开了生活的小口,斯维亚兹斯基都会恐惧、退缩,生怕这样的谈话强迫他看到自己生活的本来面貌。
然而,列文在经历了生活多重维度的启示和思考后,在见证了热爱生活却学不会怎样生活的哥哥尼古拉的死之后,他竟然转为宗教的和平主义思想,放弃了一贯延续和追求的现实之真,总不能说是进步。列文,一位有生活意识和思考意识的青年,在面临复杂的生活后从现实事务中匆忙抽身,在宗教信仰里寻求解脱,或说是逃避,而放弃现实事务的实在性,认为“一切都在为祂而活”,仿佛这样便有了最高的寄托和动机,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安娜·卡列尼娜》的拱形结构在列文与安娜相遇的一刻得到了升华。此前列文谴责凯蒂不懂得拒绝他人的示好,然而此次列文却彻底被安娜征服,完全迷恋上她,“眼中带有不寻常的光亮”,此刻人性的弱点被放得巨大:他一向自认凯蒂对他不起,自己却也不能逃脱人性的冲动。
列文和安娜,这两个不相干的人,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却都有着看穿生活虚伪本质、追求真实的品质。此前他们不曾见过面,此后他们再未重逢过;两条相交线汇聚于一点,再分离开,然后各自人海茫茫,就像每天遇见的成百上千个陌生人一样:谁也不知道谁在谁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列文是幸运的,他的求婚遭到凯蒂拒绝后,最终还是又得到了凯蒂的爱。渥伦斯基和安娜的爱却来得太晚;安娜过了八年安稳光鲜却酷似囚笼的婚姻生活。自从嫁给了大她20岁的卡列宁,她本就未开化的爱恋情感进一步被压抑了,直到见到渥伦斯基才初次萌发。渥伦斯基和安娜都厌恶虚伪,因为他们都如此的真实而摒弃做作的生活,与麻木腐败的社会如此格格不入,对种种戒律和道德束缚如此厌恶。终于,她得到启蒙追求爱情,可她没有试错的机会。因为作为有夫之妇,这是她的第一次爱情,也只能是她的最后一次爱情:身败名裂是必然,被众人掷石头却活下去是偶然。
渥伦斯基和安娜的爱起于被外表吸引,接着被彼此的内在心灵箍紧,但安娜最想要的一生的承诺,渥伦斯基给不了他,安娜也给不了自己,因为她的良心不能不时刻提醒guilty love的存在,也不能让她在离婚和儿子谢里沙之间做出舍弃。
安娜只是一个追求爱情的女人,在“系统”女子待嫁的规矩中丧失了自行了解生活的权利,嫁给了后来被她厌恶至极的卡列宁。安娜唯一不合时宜的改变就是她觉醒了;安娜最被厌弃的行为在于她不但觉醒,还迈出了打破规矩的那一步来追求爱情。卡列宁是一个无辜的人,值得同情;安娜何尝不是一个无辜的人呢?卡列宁因为先天缺乏感情而一辈子平稳如死水,安娜因为生命力和热情反而要被吊在十字架上,遭受践踏道德的指责和审判,凭什么?一个一辈子躲避爱、不敢去爱的人固然值得怜悯,一个无法忽视爱情的人却要遭受剧院包厢的侮辱、其他更恶劣下流的女人的白眼,凭什么?
安娜,虽然是一个出轨的女人,但她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因此不奢求多莉能够接待她,不奢求能见谢里沙一面,不奢求彼得堡再度接纳她,而这些罪感只能源于她的强烈的道德感。在这8年的婚姻中,安娜和卡列宁彼此了解、彼此尊重、以礼相待,安娜不但对卡列宁有感情,且一定尝试去爱卡列宁。可是她无法爱。安娜被姑妈安排了命运,少女的无知、习俗的强大,这一切都让她没有选择。一位被安排了命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挣脱枷锁呢?在彼得堡谴责安娜违背了道德时,谁又想过回到8年前,告诉那时的安娜·奥勃朗斯卡娅生活的真相呢?
安娜的第一次爱情,因为缺乏经验而一次次遭到戕残。冷战、拒绝沟通,这是爱情的大忌;明明宽容却因自尊而脸上写满冷漠,筑厚了两人间的石墙;不理智的妒忌,极端的占有欲,使得爱情不受控制地泛滥,淹没了安娜的智慧,而这智慧本可以让安娜懂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供养,而不是一个人的索取;将一切与爱情捆绑而丧失了自我的生活空间,才会有“除了你(渥伦斯基),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安娜在最美好的爱情面前,却一次次陷入遗憾、痛心而无法逃离其间的怪圈。
渥伦斯基被安娜捆得越紧,就越是想保有自己的事业。“不提醒一个盘腿而坐的人,他也许能一动不动坐上几个小时;可你一旦提醒他不能动,他就几分钟也坐不下去。”安娜是弱势的女人,一旦放弃与原有的生活和名誉就不得不赌上自己的一切;可渥伦斯基是家庭的顶梁柱,他要有自己的事业,要在贵族选举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为他和安娜“未来的儿子”经营广袤的封地和万贯的财富。甫一逃离彼得堡,他不能不在绘画、修建医院中逃避guilty love造成的情感缺憾,但作为男人,他也知道逃避对他和安娜都是毫无助益的。安娜的任性叫他绝望;一旦爱情成了博弈,悲剧结局便昭然若揭。爱情无法衡量,所有的攀比都是在糟践它,所有的冷漠都是在毁灭它。爱情中的许多时刻,坚持了自尊,就是放弃了爱情;另一方面看,爱情本就是放弃极高大自尊后的强烈快乐,一种暴露软肋的危机感,一种敞开软肋的信任感。
美丽、智慧的安娜,被爱情冲昏了头,可她别无选择;这个社会把她逼到了绝境,劝安娜苟活,可骄傲的安娜抬头挺胸了一辈子,她拒绝苟活。
渥伦斯基值得责备吗?必然是不值得的。生在“系统”里不是他的选择,正如做一个无知的待嫁少女不是安娜的选择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选择,是历经千年形成的打不破的甬道。渥伦斯基为了他和安娜的爱放弃了许多,但从未像安娜那样想为对方放弃一切。渥伦斯基始终保留了“自我实现”这一个朴素愿望,却也不及解救安娜的下限。渥伦斯基想要的是一种平衡,作为一个被社会宽容的男人,他有许多可以追求的,不到事态崩溃的那一天,他永远会在徘徊,认为有余地可留。但是安娜已经没有可留下的余地了,她为渥伦斯基放弃了最重要的一切,而渥伦斯基的有所保留让她心凉。
倘若增强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完全可以认为安娜的出轨是一件并不严重的事情。她自己若是能放得下一整个外界。对那些给她白眼的女人报以白眼,她也就挣脱了活在别人评论里的日子。但归根结底,安娜强烈的道德感不容许她做一个堕落的女人,哪怕她时刻暗示自己去原谅自己的错误。出轨就是出轨,这并没有可辩驳的。安娜身上的这种冲突在当代的科学家、文学家的流亡中清晰可辨,社会约束和追求的矛盾最终撕裂了他们。
安娜是可以被责备的吗?当然是可以的,如果可以责备一个小女孩的话。安娜的偏执到极点的爱情、放大局部看来宁折不弯而纵观全貌却无比癫狂的情绪,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作死行为”,引领她走向令人叹息和恼怒的境地,可真的要用死才能抵偿她的错误吗?难道世界上所有悲惨后果掺杂了咎由自取的成分,就注定要以死相抵吗?
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始于车站的惊鸿一瞥,自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那时他们的爱情多么惊心动魄而满载着激情啊;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也终于车站的铁轨铁轮,那颗照亮了安娜生命之欢乐的蜡烛——爱情之烛——随着安娜的卧轨而闪曳熄灭,没有爱人的陪伴,没有旁观者的同情,没有美的残留,只有死亡,在死亡面前,包纳一切的虚无都显得渺小。
安娜从开篇时的美丽聪明有所追求的贵妇人,变成了篇末残缺不全的尸体;渥伦斯基从开篇时意气风发的伯爵老爷,变成眉宇间不时流露出难忍痛苦神情的受伤男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岁”,将要把自己送往土耳其战场,再也不回到这片毫无牵挂的土地。
安娜的死无法归咎于任何个人。贝特茜是最堕落的小人,她对安娜的指摘实则出于自我保护和对社会规则的维护,却很难说是她导致了安娜的疯狂;渥伦斯基的嫂子良善温柔,可她照样对安娜关上了大门,因为她不能只顾及渥伦斯基的尊严,还要顾虑家庭的名声;无论安娜是否值得同情,渥伦斯基的母亲也不会愿意儿子和名声败坏的女人在一起,尤其是儿子竟然为她放弃了大好前程;多莉和凯蒂也无法接待安娜,因为她们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家人与她处在同一屋檐下,被“系统”戳脊梁骨。
安娜的爱情燃亮的那一刻,她已经自绝于这个社会。但是这样的安娜,也只能有这样的结局。托尔斯泰呈现了这出悲剧却没有作任何褒贬,因为这个世界仅作为一个实在而出现,不接受任何的褒贬。我只能知道这里有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生命——而不是那些如同僵尸的生命——因为两种正确的执念而撕裂了自己,而世界只是在旁观,没有制止,没有同情的人伸手。
读托尔斯泰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有一种内在的激情,一种与众生共情的悲悯感;读托尔斯泰时,脑海中是大写的人,书页中是人类的善良在讴歌、贵族的尊严在起舞,托尔斯泰这个老头在用爱书写他的道德律和伦理观,反映的却是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真实。
应该不会再写托尔斯泰的书评了。《安娜·卡列尼娜》《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而后两者的篇幅很难再写一篇长评;其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在托尔斯泰着力表现的历史观中完全丧失其自主性,人类光辉变得模糊不清;《复活》中延续的列文余音则体现了一个被教条和传统禁锢的人可以腐朽成什么样子。
可偏偏就是这本1877年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在托尔斯泰49岁时被完成;《安娜·卡列尼娜》有自然优美的文体,不矫饰、不炫耀,少年读之能安心气,长岁读之则更悠长。列夫·托尔斯泰可以凭借它永垂不朽了。
转自:搜狐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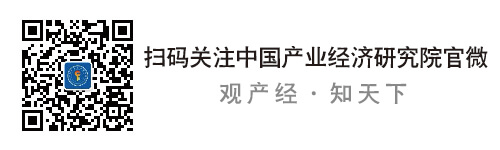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