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翻开《悲惨世界》,雨果笔下19世纪法国的苍凉画卷仍能瞬间将我裹挟——阴湿的监狱石墙、巴黎街头的寒风、巷弄里饥寒交迫的孩童,每一处细节都浸透着苦难的重量。但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史诗,从未将读者困于绝望的泥沼。当冉·阿让握着卞福汝主教赠予的银器走出教堂时,黎明的光洒在他身上,也照亮了全书的灵魂:在极致的苦难中,人道主义的救赎之力终将冲破黑暗。合上书卷,那些关于宽恕、坚守与爱的故事,让我对人性与家国社会的意义有了更沉厚的思考。
《悲惨世界》最震撼人心的,是“救赎”二字贯穿始终的力量。冉·阿让因偷一块面包被判十九年苦役,出狱后满心怨怼,是卞福汝主教“把这些银器拿去吧,它们是你的了”的宽恕,彻底击碎了他心中的坚冰。从此,这个曾被苦难扭曲的人,化身为“马德兰先生”,用财富创办工厂、修建医院,在海滨小城成为人人爱戴的市长。当沙威警官穷追不舍,揭穿他的身份时,他本可弃逃亡的芳汀于不顾,却坚持送她的女儿珂赛特去巴黎;当革命爆发,他冒着炮火潜入街垒,救出沙威后又选择放他一条生路。这种从“被救赎”到“救赎他人”的蜕变,让我明白:苦难或许能摧残人的肉体,却无法泯灭人性深处的良善,而一次真诚的宽恕,足以唤醒一个灵魂的新生。就像主教临终前所说“永远不要报复,要爱你的敌人”,这份超越世俗的慈悲,正是对抗苦难的最有力武器。
如果说救赎是个体的精神觉醒,那么书中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刻画,则藏着对家国社会的深刻叩问。芳汀为养活女儿,卖掉头发、牙齿,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她的悲剧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封建专制下底层女性的集体悲歌;小伽弗洛什穿着不合身的破衣服,在街头流浪,却在革命中勇敢地为战士送弹药,最终倒在炮火中,他的夭折是时代对童真的碾压;无数失业工人在街头乞讨,在饥饿与寒冷中挣扎,他们的苦难直指社会制度的腐朽。雨果没有回避这些黑暗,他用细腻的笔触写下“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字字泣血地控诉着不公。但他从未放弃希望,通过冉·阿让的善举、革命青年的理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爱情,在苦难中种下光明的种子。这让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进步,从来离不开对底层的关怀,离不开每个个体对正义与良善的坚守,家国的温度,就藏在对每个生命的尊重里。
《悲惨世界》最具温度的,是人性中闪耀的坚守与温情。冉·阿让抚养珂赛特长大,为她遮风挡雨,在她出嫁后默默退到幕后,这份“父爱”无关血缘,却深沉如海;沙威一生信奉“法律至上”,却在冉·阿让的宽恕中陷入信仰崩塌,最终跳河自尽,他的挣扎让“正义”有了更复杂的内涵;革命青年马吕斯,从最初的愤世嫉俗到后来的为爱坚守,在街垒战中与珂赛特的爱情,成为苦难中的一抹亮色。书中最动人的细节,是冉·阿让临终前,珂赛特与马吕斯陪在他身边,他握着主教赠予的银器十字架,安详离世。那一刻,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平静,所有的救赎都有了归宿。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让我明白: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愿意坚守善良,愿意为爱的人付出一切,这份温情,正是支撑人们走过苦难的力量。
如今的我们,虽不必再经历冉·阿让式的苦役,不必面对芳汀式的绝境,但《悲惨世界》的精神内核依然振聋发聩。当我们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时,想想冉·阿让放弃财富救助他人的豁达;当我们对弱者漠不关心时,想想卞福汝主教对陌生人的宽恕与善意;当我们抱怨生活的不公时,想想那些在苦难中仍坚守希望的灵魂。雨果在书中写道“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这份胸怀,是对他人的包容,是对正义的追求,更是对家国社会的责任。在今天,这份精神依然重要——它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与安宁,更要心怀善意,用点滴善举温暖身边的人,让社会少一些苦难,多一些救赎的光。
合上书页,窗外的晚霞染红了天空,如同书中那些穿透苦难的光。《悲惨世界》从来不是一部只写苦难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人”的史诗——关于人的堕落与觉醒,关于人的苦难与救赎,关于人的坚守与爱。卞福汝主教的宽恕、冉·阿让的救赎、珂赛特的善良,共同构成了人道主义的光辉。它让我们明白,家国的美好,离不开每个个体的良善与坚守;人间的温暖,藏在每一次宽恕与付出里。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救赎之光前行,用善意照亮自己,也温暖这个世界。(黄智)
转自:中国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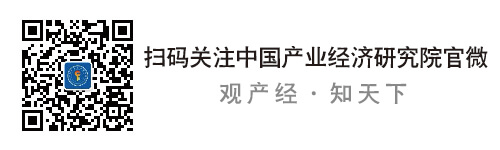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