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堂屋愈发显得空旷了。父亲走后,母亲便像一枚遗落在时光角落的旧纽扣,沉默地缀在这偌大的空间里。省城的大哥接她去住,她却总说电梯上上下下,窗外的灯晃得她心慌,不过半月便执意要回。
“顺”为孝先。我懂她,那方浸透了父亲气息、印满子女脚印的院落,才是她安放晚年的根。回到老宅,母亲仿佛重新接上了活气。她默默搬出那只落满灰尘的柳条笸箩,仔细拂去浮尘,露出里面沉睡多年的针线布头:褪色的靛蓝土布、几绺鲜艳的丝线、大小不一的铜顶针,还有一把沉甸甸的老式剪刀,刃口依旧闪着寒光。母亲很快沉浸在这方寸针黹之间。她摊开陈年碎布,对着窗棂透进的光端详纹理颜色,全凭心裁穿针引线,如同绣起无声的时光。
可岁月是位无情的染匠,一向眼明手快的母亲视力渐渐模糊。医生说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视野中央总有一团驱不散的雾。她穿针引线变得异常艰难,常常对着针鼻儿半天也无法成功。我终是放心不下,几番商议后,她同意跟我回到南方小城。
小城生活宁静。我的书房临窗,窗外花架上攀援着茂盛的紫藤萝,在春日里垂下串串紫云。母亲就时常坐在窗边,望着那片紫色出神。
我的孩子快满周岁,母亲总说要做虎头鞋给外孙,我却不敢应。“妈,眼神不好,咱就歇歇,看看花,听听曲儿。”我温声劝道。她含糊地应着,目光却总不由自主地飘向巷子里那些做针线的妇人,手指在膝头无意识地捻动,像捏着看不见的丝线。
日子久了,我忽然发现书房里那只她带来的旧笸箩换了位置,里面的布头线轴像是被人仔细整理过。问她时,她只轻描淡写地说“就看了看”。望着她避开我目光的侧脸,我心里隐约明白她对针线的念想,只当是老人闲时翻捡旧物,便没再多问。
直到某天深夜,我睡梦间被书房门缝透出的一线微弱光亮惊醒,悄悄走近,却是看到昏黄的台灯光晕下,母亲正佝偻着背伏在书桌前。她戴着老花镜,鼻尖几乎要贴到桌面。那布满老茧的手一只死死捏着一根细小的绣花针,另一只颤抖着捻着一缕金黄色的丝线,对着那几乎看不见的针鼻儿,一遍、两遍、三遍地尝试着穿引。她紧抿着嘴唇,眉头因全神贯注而深深蹙起,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每一次失败,她的肩膀就颓然地垮塌一分,但喘息片刻,又固执地再次凑近灯光。
书桌上摊着一块巴掌大小的明黄色湘绸,旁边散落着几片剪好的、同样鲜亮的红布,在笸箩边,我还瞥见一小块质地明显不同的、带着细碎花纹的深蓝色边角料——那是我前几日新买的一条丝巾包装袋上的。
我的呼吸瞬间凝滞。那些被悄悄挪动的笸箩、被细心修剪的布料,原来都不是无意为之——母亲哪是在“看看”,分明是借着这昏黄的灯光跟自己模糊的视线较劲,一寸寸摸索着未竟的针线活。
“哎哟……”我心里一紧,针尖扎破了她的食指,一颗鲜红的血珠迅速沁出,母亲却浑然不觉,只飞快地将手指在衣襟上蹭了蹭,又迫不及待地拿起针线,继续她那艰难的穿引仪式。
不知尝试了多少次,金线终于颤巍巍地穿过了细小的针孔,母亲浑浊的眼睛里骤然爆发出孩童般纯粹的欣喜光芒,她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惊天伟业。
她小心翼翼地将穿了线的针别在绸布上,然后拿起剪刀开始修剪那些小小的红布、绿布。借着灯光,我依稀看出,她正在做的是一只虎头鞋的前脸。那小小的、未成形的虎头,正对着我,呈现出一种懵懂而倔强的生机。
“小宝……虎头鞋……保平安……”母亲对着那未完成的布老虎头,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含混而温柔地低语着。
晚风从敞开的窗缝溜进来,轻轻拂动母亲鬓角散落的白发。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佝偻的身影在台灯下缩成小小的一团,像一尊被时光侵蚀却依然执着燃烧的烛台。
我悄然退后,轻轻掩上门,泪水无声地汹涌而下。母亲不再能轻松地穿针引线,甚至看不清眼前布料的颜色,却牢牢记得要给刚满周岁的小外孙缝制一双能驱邪保平安的虎头鞋。那深植于血脉、铭刻在骨子里的爱之本能,如同那枚穿透迷雾、终于引线成功的银针,纵然微小,纵然艰难,却在记忆的沉沉暗夜里,固执地闪耀着,为她,也为她所爱之人。(代慧敏)
转自:中国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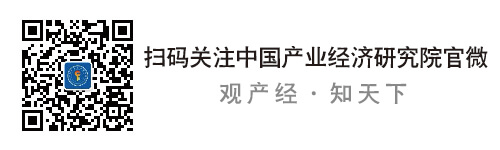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