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 夜 人
刘星元
你以为那声音是敲击梆子所发出来的吗?
那只是表象。我们习惯以表象的东西代替真实,并且始终信以为真。就如我们看到深夜时分昙花绽放只是昙花绽放,却没有发现,是有神路过了它,并在路过它时轻轻地吻了它。你问是什么神?很抱歉,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他只留给我一个背影,并且这背影也将迅速消失。他留给我的背影比任何的黑还要黑,仿佛他就是黑的持有者,但他所有的黑里一定劫持着所有的白——那朵招摇的昙花泄露了他的秘密。
好吧,现在就来说说更声。
黑夜是一面大鼓。我不认为这是个比喻。这是个事实。打更的人站在天地之间,被黑夜重复吞噬,或者说被黑皮大鼓深埋。他将棒槌击向黑夜的样子,常让我想起那些伟大或不伟大的时代的思考者——屈原、但丁、黑格尔、尼采……面对黑夜,他们用自己交换光明,并在光明到来之前一一倒下。
抱歉,我还是没有说到更声,那些具象的、醒着的更声。你要知道,文学作品中的神秘,往往源于作者的无知或故作无知,而我的拖延正是源于我的无知。我是远离更声的一代人,不必用一种原始的时间分割生命。我对更声的大部分认识——那些理解和不理解的认识,都来自于上一辈人以及更上一辈人的言说。这些言说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在家庭闲谈之中,除了消遣,没有任何功利性。作为非见证者,我无法辨析它的真伪。而且,我并不期望非要把它分出真伪,以至真者留下,伪者去之。在民间,多少事物的本身与人们赋予它的意义相悖?然而,那些与真实相悖的附加意义,却与真实的属性相安无事地活了下来。甚至,与真实相悖的东西,它存在的理由更为充分,它更为密切地贴紧了民间,让民间以神性的光辉活在历史和当下。那些草木不存在的药性,那些河流不存在的神性,那些生灵不存在的邪性,以及那些巫师的祈祷词,那些守灵的安魂曲,民间的众多事物,概莫能外。
从科学维度上看,时间就是时间,一切事物皆依附于它。但在民间维度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存在。民间的万事万物告诉我,时间是依附于它们之上的。它们存在,时间就存在;它们毁灭,时间也随之毁灭。譬如打更人以及更声。但我更愿意将打更人叫做守夜人。
如果去探寻守夜人的踪迹,我更愿意从关于众多守夜人的民间传闻里,抽丝剥茧地去书写其中一个人的故事。每个群体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我无法将那么多的特殊性一一记录在案。现在,请允许我将广阔的空间一点点缩紧:夜空那么高,大地那么广,天地之间,那么多的守夜人在民间活着,在黑夜之中穿行。那么多的守夜人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们国三十四个藩镇的守夜人,我在乎的是我们藩镇十七个地域的守夜人,我在乎的是我们地域十二个县区的守夜人,我在乎的是我们县区十六个乡镇的守夜人,我在乎的是我们乡镇六十七个行政村和二十多个自然村的守夜人。没错,我在乎的是我们村的守夜人。
我们村的守夜人已经很老了,并且还将继续老下去。他身穿黑衣黑裤,皮肤黝黑似铁,佝偻着身子在悄无人息的村子里缓慢行走。他的黑和夜的黑先是相互抵触、攻伐,继而慢慢交融在一起。他被黑夜吞噬或黑夜被他从身体里释放了出来。守夜人和黑夜,他们彼此构成了彼此的一部分。黑夜涌动,他就涌动;他静止不动,黑夜也静止不动。此刻,我描述的他就是静止不动的。他在等。等时间。守夜人的腹中,有一台刻度精准的座钟。座钟滴滴嗒嗒地在他的腹内摇摆着,走动着,一刻不停。一秒、两秒、三秒、四秒……我猜想这座钟表绝不是如此寻常地表演着时间的富裕。按照科学思维与民间思维、科学本质与民间本质的悖论这一论断,守夜人腹中的座钟恰恰是倒计时。守夜人静止不动的等待,不是时间的堆积,而是时间的消散,以至他腹内富余的时间,被广阔的天地精准地抽走。当这一轮的时间消失殆尽,守夜人就要举起手中的棒槌和木梆了。
我们村的守夜人开始打更了。更声里的讲究,是长辈们告诉我的:“咚——咚!”,“咚——咚!”,“咚——咚!”。一慢一快,连打三次,这是头更。“咚!咚!”,“咚!咚!”,“咚!咚!”。打一下又打一下,连打三次,这是二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慢两快,连打三次,这是三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慢三快,连打三次,这是四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慢四快,连打三次,这是五更。天分两极:白昼与黑夜。夜分五更:戌时为一,亥时为二,子时为三,丑时为四,寅时为五。戌时天渐黑,寅时天渐明。守夜人正是按照夜的尺度为它量体裁衣的。且不说这件衣裳是否能严丝合缝与黑夜融合在一起,但其他人却借助更声知晓了时间的流转奔腾。他们在自己的床上伴随着更声睡去,又伴随着更声醒来,只要是村庄的一份子,生老病死的生涯便与更声同在。
偌大的一座村庄,黑夜里有一个守夜人就够了,有一种沿着时间刻度行走的更声就够了。作为此地的村民,我们其实只是村庄的寄居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说,我们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侧面,而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正是守夜人。当晨昏被人为或非人为地分成两极,我们的晨与守夜人的黑便各自占据了天平的两端。那么多那么多的我们,与那么少那么少的守夜人,坐拥着同等的重量,谁都不可能离开谁。一个侧面离去,天平就会急速倾斜,将另一个侧面甩入万丈深渊。因此,我们才专心持有着白,守夜人才一心一意陪伴着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
我曾在本地的一位民俗收藏家那里看见过守夜人打更的工具。和别处的锣鼓不同,本地打更用的是梆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江苏梆子……你一定听说过这些以梆子命名的地方戏曲。戏台上,小生涂粉描红,文文弱弱的;青衣长袖如云,轻轻缓缓的;花旦华服雍容,端端方方的……故事无非是赶考的举子、怀春的闺秀、慷慨的忠良、圆滑的佞人、桀骜的奸臣、耍乐的丑角……戏中人物随着乐器的响声上台来,随着乐器的响声唱起来,随着乐器的响声舞起来,随着乐器的响声耍起来。乱哄哄的一场戏,演的人仔细演,看的人却未必认真看;唱的人认真唱,听的人却未必认真听。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上的小戏种,就是要演给地方的小老百姓听的。乡人们看得热闹,听得舒服,比什么都重要。啰哩啰嗦说了这么多,当然不是在说戏,我是在说那戏中最为紧要的乐器:梆子。关于梆子,我查到的资料是:一般多用紫檀、红木制作,材料必须坚实、干透,不能有疤节或劈裂。外表光滑、圆弧,棱角适度,常应用于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民间器乐合奏。以梆为戏也颇有些历史,清代戏剧家李调元在他的《剧说》里说: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
我眼前的梆子,却不是名贵的紫檀或红木质地。它用的是枣木。我记得身为老木匠的祖父曾教授过我:枣木质地坚硬密实,木纹细密,虫不易蛀,尘不易磨。乡间无良木,这枣木就是难得的好材料,以枣木为梆,倒也合适。枣木梆子由两部分构成:一为槌,一为梆。梆子有些年头了,大概是晚清或民国年间的老物什,槌柄和梆面受到守夜人日复一日的手磨,已经凹入许多。许是保养的还算妥当,红中透黑的木头上,竟然没有一丝裂纹。枣木自身的纹路,似柳条,似卷花,似水纹,似轻云,随意地贴在木头的皮肤上,似乎轻吹一口气,它就要飘走。轻轻敲打了它一下,以槌击梆,就像是庙中和尚敲打了木鱼,柔软的香气就包裹着清亮的声响,从木头里钻了出来。
让我们再回到那具梆子的所有者,回到黑暗处的守夜人吧。对于守夜人,虽然俗不可耐,但我确实没法用别的什么词来替代“神秘”——这并非是因为我语言的匮乏,纵使我饱读了天下之书,依然无法找出更为精确的词语来表达。况且,我内心实在不愿让这个词在笔下逃脱。我擒住了它,并试图以此擒住关于守夜人更多的故事。可我也知道,所谓神秘,无非就是用一些实物或虚物、具象或抽象的东西遮蔽另一种东西,而一旦揭开这种遮蔽,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因此,我又是矛盾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心爱之物,既想炫耀,又不想与别人分享。我既想以文字的笔尖抵达神秘的守夜人的最神秘之处,又不愿意这种神秘因为我的贸然来访失去自己的色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很长时间,我被这对矛盾所撕扯,患得患失,以至于裹足不前。守夜人以及守夜人更多的故事,被埋在我乡故老的心里,随着他们慢慢老去,慢慢死去。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虽然神秘因此而更为神秘,但是也因此渐次消失。世间的神秘,又有多少是能够揭开的呢?时至今日,放弃我的自以为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守夜人,就算我倾其所能尽其全力,恐怕也无法探寻到这段传奇的十之三四了。或许,也正因为只能探寻到这段传奇的十之三四,才更能持续地保有它的神秘。这样看来,恰在此时走近它,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意”。尽管我始终对非自然的命数持怀疑态度。
和“神秘”这个词一样,我是说,“天意”这个词,我自忖尚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可以替代。好吧,那就以“天意”的名义,高举从我乡故老口中燃起的即将油尽灯枯的火把,让我们接着走进神秘的守夜人。
偏居村庄一隅的那座院子,它窄小,低矮。院子委身于树木和藤蔓间,浑身透着一股子阴凉。两扇用黑漆浸染的榆木大门有些年头了,表层的漆皮多处脱落,露出下一层的油漆。下层的漆皮更为黝黑。我很少见过那样的黑——与通常的黑色不同,那是一种密不通风的黑,好像在排拒什么进去,又好像在阻拦什么出来。院门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一直想知道,却始终都没能知道。那是我们的禁地,长辈们曾耳提面命,三令五申,严禁我们走近它。我们之所以没有走近,却并非长辈们的禁止,而是由于恐惧。人们对于黑暗的恐惧究竟是来源于动物的本能还是后天的教育呢?我不知道对于那座院子的惧怕从何而来,但我却知道那座院子的主人是谁。当然,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对黑夜充满崇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黑暗的化身。没错,那就是守夜人的院子。
那扇院门从未打开——这是我的所见;从不知院子里发生过什么故事,这是我的所闻。也就是说,除了一座院子就是一座院子外,我对这座院子一无所知。
我接下来要叙述的所见以及所闻,皆来自我的祖父年轻时候的经历。他将自己的经历转述给了我。他说,他也从未见过那扇院门打开过,但是某一年秋天,他发现黑黝黝的院门上竟然贴起了对联,挂上了红字。祖父说,那是守夜人家里有喜事了。按照更年长的长辈们的说法,守夜人是一种十分庞大的人类类属,虽然每村只有一户这样的人家,但扩大至乡至县至省,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微弱的存在了。守夜人与我们是不通来往的,他们拥有更为单一和牢靠的人际关系,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他们的婚丧嫁娶,是守夜人与守夜人之间的婚丧嫁娶,和外界无关。院门上贴了喜字的守夜人,必定迎娶了其它村子里守夜人家的姑娘。嫁与娶没什么好说的,值得一说的是,办理婚娶大事,他们竟也做得不动声色,真是不可思议。倘若不是及时发现了那些喜字,倘若喜字被风刮去被雨淋掉,将无人知晓这户人家的一件人生大事,已经静悄悄完成。这件事引起了村人们对于守夜人家族更大的好奇,他们更为留心这个家族的一举一动。此后,有人在院子周围发现了一小片菜园,菜园里种满了肥硕的白菜,显得比村里任意一家的白菜都更高大一些。村里没有人承认那是他们自己的菜园。接着,田野里几块种满庄稼的无主的田地浮出水面,于是我们知道了,守夜人也需要吃五谷杂粮、菜蔬果品。还有人在院门外的小道上发现了一堆倒掉的中药渣,村里也没有人承认那是自己所为,于是我们又知道了,守夜人也有生老病死,在时间和疾病面前,他们和我们拥有一致的无助。再后来,守夜人的门前又多了一面红色的旗子,旗子之上,斜挂着一张柳条儿弯制的弓箭,于是我们又知道了,守夜人家里添了男丁……
祖父讲述这些的时候,我是羡慕的,因为这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祖父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打更,提到更声。也就是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更声就停了下来。始终不明白,曾经繁盛千年的打更行当,为何顷刻之间就销声匿迹了。后来想明白了:守夜人打更,无非是将时间毫无保留地推给村庄以及村庄里住着的一切生灵。当更为精准的计时工具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更声必然会落幕,任何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概莫能外。虽然很悲伤,但也不得不说,守夜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价值,他们的销声匿迹,是必然。
做了一个梦。天地之间,篝火熊熊燃起,篝火前,身穿兽皮的部落头领带领着一大批同样身穿兽皮的族众,与另一位身穿兽皮的年轻人在举行一种庄重的仪式。头领与年轻人共握一把刀,将寒光插入牛颈,牛颈血流如注。随从用黑陶大碗将浓郁的血液接住,恭敬地呈到头领与年轻人面前。巫师在吟唱祭词,众人肃穆而立,风吹过火焰并吹高了火焰,头领与年轻人高举陶碗跪下来。他们举碗祭天祭地祭火,在天地火之间,两人将碗中之血一饮而尽……我明白,这是一种远古的契约,一种无限真诚的诺言。契约已定,年轻人带着家人,转至幕后,转入黑暗之中,并渐渐被世人遗忘。从此之后,这一户人家的职责将是守夜。他们将世世代代与黑夜为伍,世世代代为另一个维度的族人报时和报警。而余下的人将继续征伐,在白日之中,创建所谓的历史和文明——没错,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颜色当然不会依附于情感,情感也不会依附于颜色,所有颜色与情感的联系,只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倘若单纯以黑与白代替坏与好,那才是颠倒黑白。
后来读到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我怀疑这个奇幻作家也做过和我相同的梦。乔治?马丁的梦境里有个守夜人军团,他们驻守在维斯特洛的北境长城上,为阻挡长城以北的野人以及传说生物而存在。他们穿着黑衣,被称为“黑骑士”或者“乌鸦”。我愿抄录下那些守夜人的誓言: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我愿抄录下那些守夜人的悼词:他的守望至死方休,于斯结束。
多幸运,乔治?马丁和我,各自持有一段关于守夜人的故事。多悲哀,乔治?马丁的故事的最后,守夜人一直还在,而在我的故事的最后,院子已经荒芜,我不敢确定里面是否还住着那些神秘的守夜人。
他的守望至死方休,于斯结束。更声已经停了下来,他们的守望结束了吗?
我只问,不答。
——原载《散文》(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刘星元,1987年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炜工作室学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天涯》《钟山》《红岩》《散文》等刊,散文集《尘与光》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山东文学奖、孙犁散文奖、长安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
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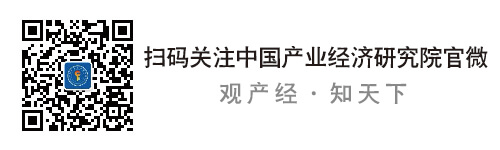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