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止了奔跑
刘星元
火车停止了奔跑。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依次地慢下来。就好像一条渐次接近死亡的毛毛虫,它用越来越微弱的力量,想要带着自己的命逃窜,却在逃窜的途中用尽了力气。
它爬行的速度越来越慢,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终于,爬不动了。它的触角和身体都在慢慢变得僵硬,僵硬的它像一条黑色的枯枝,横陈于大地之上。
火车一停下,车厢内的人群就骚动了起来。从远处看,透过密集的小格子车窗,车厢内那骚动的人群,就像是依附在庞大的毛毛虫身体内的细菌和走虫,他们在它的体内活泛了起来。
有人从睡梦中醒来,开始闲聊;有从座位上站起来,活动了几下筋骨;也有人带着行李穿过人群和车厢,一个人默默地走下火车,走下站台。而我往往就是那个默默地走下火车的人。
图片
而我往往就是那个默默地走下火车的人
这是一座坐落于县城西北方向的小站,被县城用手拢了一下,但并未完全陷入县城的躯体内。就像是一个人身上的黑痣,它依附于人,却又独立于人。
因为依附于大村落似的县城,上车的人少,下车的人也少,以至于显得冷清。月光明亮,那些明亮的月光,不动声色地洒在车站的办公楼上,洒在站台上,洒在停下来的火车上,把这些物件一一擦亮,并让人记住了它的慷慨和野心。
月光洒向铁轨上却不是这样——铁轨依附且平行于大地,不断地沿着大地的脊背延展,月光那么软,铁轨那么硬,月光捶打在铁轨上,却像是捶打在软绵绵的棉花上一样,那些玉质的光华,被铁轨吸进了身体,再不释放出来,以至于阳光与铁轨相处最近的那一层虚空里,构成了一种浓密的黑。
你无法理解,我是多么喜欢那一种在任意一处所在都无法捕捉到的黑。
那种黑最初来源于电影,乡下的露天电影。多皱且陈旧的幕布之上,一列火车喷着蒸汽,从我的眼前驶过。火车向着远方行驶,只留给我一个默默糊糊的背影。火车的背影沿着铁轨跑动着,它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整个过程,唯一不模糊的,就是火车与铁轨相交处,那一层无限浓密的黑。
我的目光盯着它,盯着它将火车赶向了远方,盯着它安静地浮在没有火车的铁轨上。它是那样的神秘,它的神秘,将我眼睛里欢悦或忧伤的那些小光亮,一点点吞噬了进去。
梦里,那列火车在一次次飞驰,咔嚓咔嚓,就像是压碎月光而发出的声音。火车一次次经过我,火车经过了我,却没有停下来。天地之间,只有一条铁轨横在那里,横向远方;铁轨旁边,只有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望向远方。脑里心里,只有那咔嚓咔嚓的声音还在不断传来。
图片
梦里,那列火车在一次次飞驰
腊月的最后几天,邻居家的三叔回来了。三叔在甘肃当兵,一年也只能回来一次。我不喜欢他穿着军装扬着脖子时的那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喜欢他与亲友们交谈时使用的时髦的普通话,不喜欢他在故事里一次次把自己刻画成一个世间少有的英雄。
但我必须承认,纵然有那么多的不喜欢,我还是很喜欢他。因为,我喜欢他给我们讲火车上的一些趣事、奇闻,尽管这些故事真假难辨;因为,我喜欢他刚回来时那一路的疲惫样儿,那样子告诉我他确实是乘坐火车回来的。
三叔给我讲过关于火车的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没有忘记的是三叔的承诺。三叔说,等我稍微再长高一点儿,也带我去坐一次火车。没有哪个少年能够抵挡住这样美好的诱惑,对于三叔的话,我的确是当真了。
“再长高一点儿就能坐上火车”这样一个荒谬的句子在我的心里发酵,冲撞,像一种更为原始的性欲,挑逗着我的少年时代。
为了长高,我在学校的单杠上不断伸拉自己的身体,在深秋的河水里不断摆动自己的四肢,我甚至听信了本地由来已久的传说,一次次站到后院的那棵老椿树下。我抚摸着椿树一遍遍默念: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来好做梁,我长长来穿衣裳。
三叔最终也没能兑现他随口说出的承诺。第二年秋天,部队上来的人敲响了他家的院门。他们给三叔的家人带回来一张《烈士证明书》和一套三叔崭新的军装。军装上金属的纽扣在阳光的摩擦中,亮出了耀眼的光芒,晃得人眼晕,心疼。在此之前,没人会想到,三叔最后一次坐着火车回乡,竟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坐上梦寐以求的火车,已经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候正是火车的旺季,人多。我怀着兴奋中略带些忐忑的心情走进县城的火车站,走上站台,在一群人的推推嚷嚷中挤进了车厢。没有座位,但这丝毫不能消减我内心的兴奋。我的兴奋无处宣泄,只能由着一双米粒大小的眼珠儿左顾右盼。
我要去的城市叫作济宁,是盛产圣人的地方,我总觉得,此一去,不混个圣人当当,也该混个贤人做做。结果是,余下的几年,那座城市以大学的名义挥霍了我的三年青春,只抛给我一张单薄的毕业证书,就把我给打发了。于是,我又回到了本地的这座小县城,并在此定居了下来。
县城是安分的,它更适合收容一个人的下半生——它擅长用这份安分消磨一个人的野心,宽慰一个人受伤的身体。对于一个生性散淡的人而言,它的安分,于我再贴切不过。
我慢慢爱上了这种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生活,只是偶尔才会在心头蹦出一点儿不甘。这种不甘是微小的,无足轻重的,它无力改变什么,顶多是打搅了一个人淡泊的心境,来一次王子猷式的出走。
当然,来去之间,最贴心贴肺的依然是火车。缓慢地向前推进的火车,于我,有一种天然的无可修饰的复古的美。而这种美,其它交通工具是没有的。
已经是绿皮火车的没落时代了,何况是一条边缘线路。沿途上车的人不多,下车的人也不多,车厢里空荡荡的,反而少了一些喧闹的干扰。这样的空,映照在心里,却是满满的富足。
图片
已经是绿皮火车的没落时代了
我一次次把县城郊区的火车站作为始发地,一次次把火车上靠窗的座位视为路途中的不二位置。铁轨铺在大地的稍高处,而缓慢行进的火车又高于铁轨。窗外,远处,是我生活的小城。
当我以这样恰到好处的高度和速度去审视一座收容自己躯体的县城的时候,它原本的熟悉渐渐消退,直至到达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天知道我为何会如此喜爱这种微微隔膜出来的感觉,就像是一种还未彻底绽放的花朵隐约散发出的味道,我的心时常会浮起淡淡的甘美。
车窗之外,我甚至隐约可以看到我生活的那个区域,它刚好出现在我背离这个城市的方位,火车一旦开动,我就只能回头看它,看着它离我越来越远。
于是,像病源的转移,它由我的视线,转移到我的心里,随我踏上又一段略带颠簸的旅途。总是这样,刚刚出发,我就开始怀念。
每一次旅途都将预示着归途。一次一次,我从一座小县城的火车站出发,随着火车跑起来;一次一次,我又将目的地设置成那座小县城的火车站,安心地等待那列火车慢慢地停下来,伏在大地之上,如一只僵死的虫。像一粒微小的细菌,我又从那只死去的虫子的身体里爬了出来,潜伏到这座县城的某个角落。
转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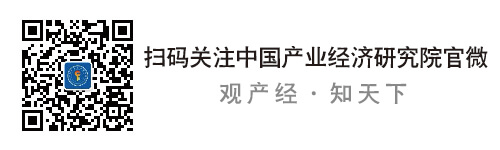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